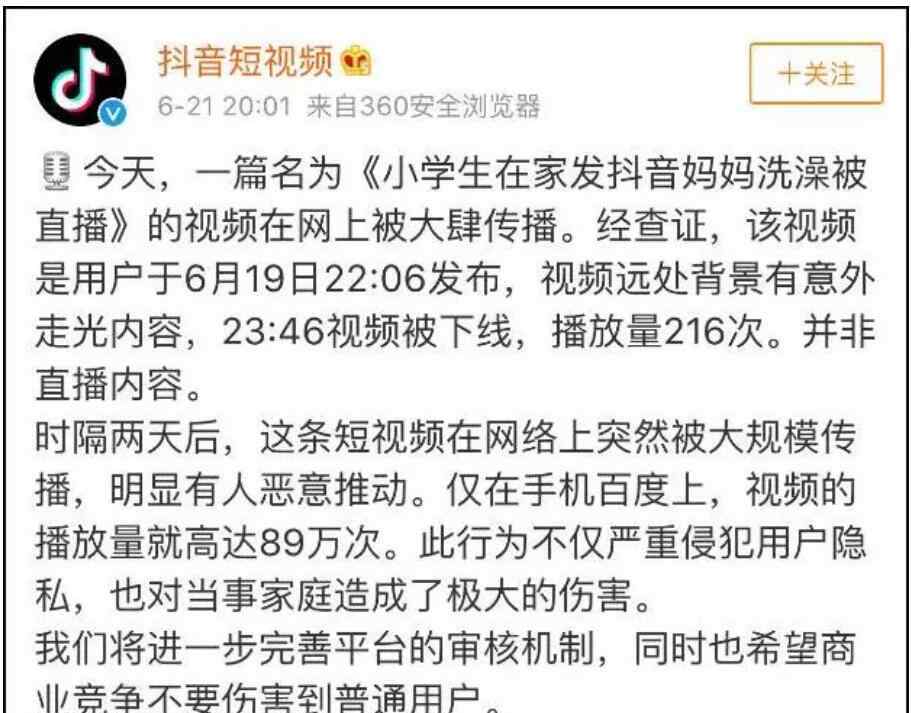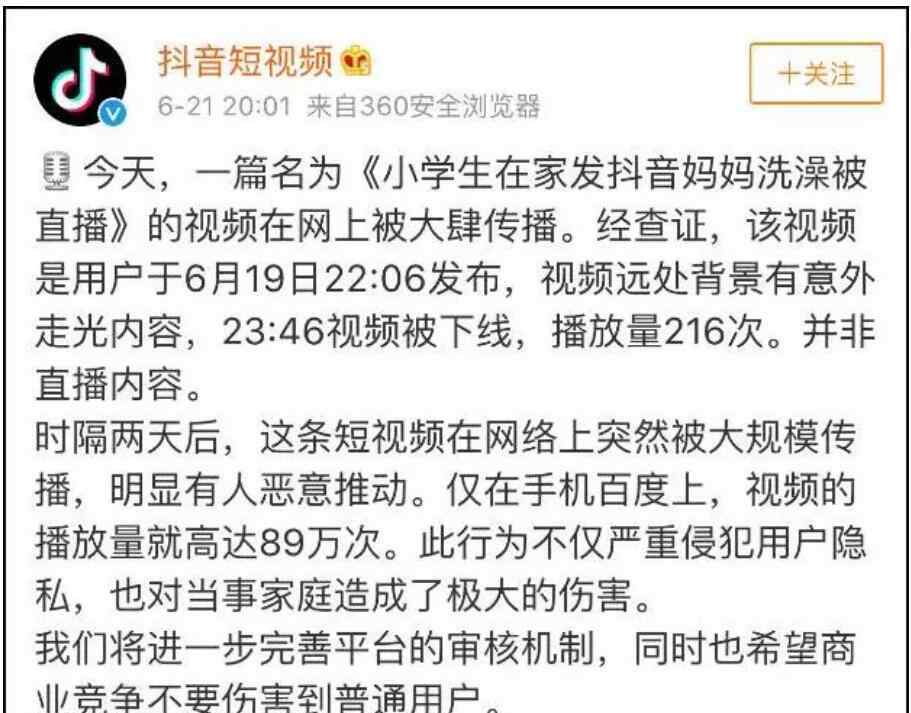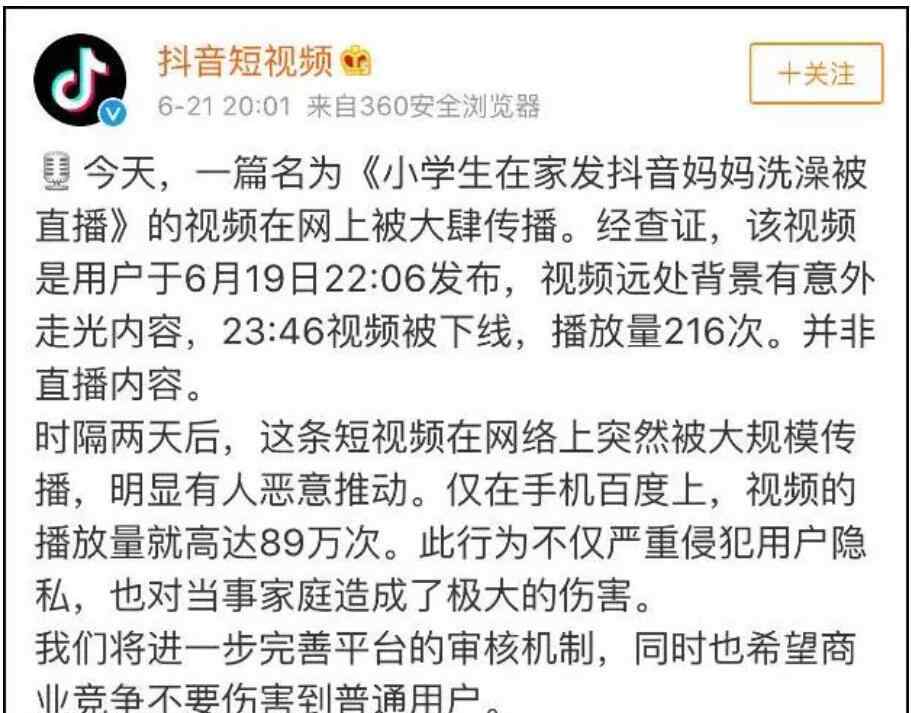译者简介:
李(1983-),讲师,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现代文学。出版有《森氏短篇小说集》、《稻草人》、《沙面》空海等六部译著,出版有《第二外语日语专业研究生学习》等两部编著,出版有《武田泰淳的战后中国经历》等六篇学术论文。
金的专业是哲学。
说到哲学家,一般都是写书什么的。金虽然以哲学为职业,但他不写书。据说他文科大学毕业的时候,写了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题目是苏格拉底之前的道家与希腊哲学的比较研究。从那以后我就没写过东西了。
但是,既然哲学是一门职业,那就要教书。他负责哲学史课程,讲授现代哲学史。从学生的评价来看,金晶的课比写了很多书的课更有趣。他的课很直观,有时候就像是在什么东西上投射一束强光。这时,学生们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经常用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来解释一个问题,让听者顿悟。据说叔本华会在资料书中记录报纸上的小道消息等轶事,作为自己研究哲学的材料,而金则会把一切作为研究哲学史的材料。他有时会在严肃的哲学课上引用年轻人经常读的小说,这让学生们大为惊讶。
他读了很多小说。看报纸或者杂志的时候,他不看任何评论,只看小说。但是,如果作者知道读小说的目的,肯定会生气。他并不把这些小说当作艺术品,因为金对艺术品的要求很高,而这些小说又达不到他的标准。金感兴趣的是作者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写这样的东西。因此,在对金的解读之后,作者本来是以悲壮的心情写东西的,但却让人觉得很滑稽,而以滑稽的笔调写出来的东西反而让人觉得悲哀。
金有时想写点什么。虽然我以哲学为职业,但我不想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什么的,所以我不想写哲学。他更喜欢写一些小说或戏剧。但是,由于他对艺术作品的要求很高,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此期间,夏目·伊藤[2]开始写小说。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之后,金感到心里痒痒的,又渴望尝试一下。然而就在这时,有人模仿夏目君的《我是猫》,写了《我是猫》,出现了《我是狗》等等。金看了很反感,最后什么也没写。
很快,出现了一股自然主义的浪潮。金看这种类型的作品并不觉得特别怕痒,但他觉得很有趣。正当金觉得有趣的时候,想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每次看自然派的小说,看到小说里的人物都伴随着对性欲的描写,批评家也把这当成对生活的真实反映,金就会想:生活真的是这样吗?同时他也在想,会不会是他偏离了正常的心理状态,生来就不正常,属于所谓的性冷淡?他的这种想法也会在阅读左拉的小说时产生。但是,当我看到《萌芽》这样的作品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描述的是一个部落工人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想要偷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幽会。这时他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特意写这段?他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可能有这种事,但他对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有疑问,也就是说,他只是认为这是作者个人的性描写爱好是否变态。可能小说家或者诗人之类的人性欲不同。这个问题也和切萨雷·龙勃罗梭提出的天才问题有关。莫比乌斯学派把著名诗人或哲学家作为精神病人逐一讨论,其依据也在这里。然而,日本最近兴起的自然学派与此不同。许多作者蜂拥而至写同样的东西。批评家认为这就是生活,这是公认的。按照精神病医生的话来说,这种所谓的生活就是每一种描述中的性欲的样式。所以,这加深了之前基奈君的疑惑。
不久之后,龅牙龟事件发生了。一个叫龅牙龟的工匠,喜欢偷看女澡堂,有一次跟踪一个女的从澡堂出来强奸了她。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常发生,是极其常见的事件。如果西方报纸在一个小角落里最多发两三行的消息。然而,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一度成为大问题,并与所谓的自然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出现了自然主义的另一个名称,“龅牙龟主义”,“突突る[5”作为动词流行起来。金现在认为,只要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色情的,他们就不会怀疑自己与众不同。
一天,金在课堂上看到一个学生带了一本名叫《耶路撒冷哲学导论》的小册子。下课后,他拿起书看了看。他问是什么。学生回答说:“我在南江堂书店看到的。我以为可能可以当做参考书看,就买了。我还没看过。有兴趣的请收回。”金借的,那天晚上刚好有空,就看了。当读到金的这一部分美学理论时,大为惊讶。书上说:“所有的艺术都在说话。性欲应该向公众发泄。这样,就像经血找不到出口,有时从鼻孔流出一样,性欲也会变成绘画、雕塑、音乐、小说剧本。”在惊讶的同时,金心想:这家伙的想法真的很奇怪,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个理论向前推一推,说明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性欲的表现呢?根据这个推理,可以得出结论:一切都是性欲的表现。最容易把宗教解释为性欲。其实很多被尊为圣人的尼姑只是把性欲发泄到一个不正常的方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做出所谓奉献行为的。如果戴上性眼镜,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力都来源于性欲。“Cherchez la femme[6]”这句话似乎可以适用于世界上的一切。金心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恐怕自己必然会被排除在普通人之外。
因此,金长期以来的写作欲望开始转向不同的方向。金想到性欲是如何一步步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它与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关系,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献似乎很少。在艺术上,像情色画一样,任何国家都有色情。然而,这些都不是严肃的作品。爱情在所有诗歌领域都有描述。然而,即使爱情与性欲密切相关,也不能等同于性欲。有些材料可以在法庭或医生的记录中找到,但大多是性变态。卢梭在《忏悔录》中非常坦率地记录了许多事情。他曾经写道,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被兰贝尔小姐打了屁股,因为他不记得他教了什么。因为他从中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假装不清楚自己所知道的,故意搞错,让兰贝尔小姐打他。然而,我不知道兰贝尔小姐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所以她不再打他了。这是性欲的初步萌发,但绝不是初恋。另外,在他青春的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性欲的内容。但是因为毕竟不是以性欲为主写的,所以读起来并不尽如人意。卡萨诺瓦可以说是纵情一生的男人。他的自传是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大部分都表现了他完整的性欲,没有一部和爱情有关。但是,就像拿破仑的大喜过望心理远超常人一样,他的自传很难作为研究名利心理的素材,而作为性欲英雄的卡萨诺瓦所写的东西也很难作为研究性欲的素材。再比如罗德斯岛的巨像和奈良佛都不适合研究人体。虽然一直在想写点什么,但是不想步前辈的后尘。也许我会借此机会写一写我性欲形成的历史。其实我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我的性欲是如何萌发和发展的。也许我会试着写这个问题。白纸黑字写清楚,对认识自己会更有帮助。这样你就可能知道你的性生活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当然,我不知道会是哪一个,才会写。所以,不知道写完之后能不能公开。总之,空有空就写一点。金这样认为。
这时,从德国发来一封邮件,邮件来自一家经常送书的书店。有一篇来自某社会的关于性欲教育的研究报告。称之为“性”似乎不合适,因为性的意思是“性”,而不是“性”。但“性”这个词是一词多义,所以加“欲”字更清楚。问题是,在教育领域,是否有必要进行性欲教育,即使有必要,能否进行?某学会邀请了一位教育家、一位宗教学者、一位医学家,他们都可以算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物,在咨询了他们之后得到了这份报告。虽然三人讨论的方向不同,但对于性欲教育是否必要和可行,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他们有的认为应该在家庭中进行性欲教育,有的认为应该在学校中进行,都认为应该进行并且能够进行。关于时间的选择,当然是在懂事之后。婚礼前给新人看春宫的照片也是中国的惯例,但应该比这个早。之所以要提前,是因为如果等到即将到来的婚礼之前,后面就有问题了。报告从低级生物的繁殖开始,逐渐延伸到人类。虽然是从低级生物开始,但是只讲植物的雄蕊和雌蕊,然后说动物和人类也没用。人的性生活也要详细讨论。
看完之后,抱起金的胳膊,想了一会儿。金的大儿子今年将高中毕业。如果他想教育他的儿子,他正在考虑该说些什么。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问题越具体,他越觉得自己的字差。因此,当他想到要把自己的性生活史写下来的时候,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把它写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在考虑你写的东西能不能给别人看,能不能公之于众之前,你要先检查一下能不能给儿子看。金这样想着,开始写——
这是我六岁的时候。
那时,我住在中国的一个小镇[8][7]。因为县城荒废了,县政府迁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下子就萧条了。
我父亲和他原来的主人去了东京。我妈觉得我不算太年轻,应该先教点知识再送去学校,所以每天早上都教我学假名,练习写作。
我父亲本来只是一个管事的人,但我们还是住在土墙环绕的临街房子里。大门前是护城河,另一边是御仓。
有一天,我学习完了,看见妈妈在纺布,我就说“我去玩了”,跑了出去。
我家附近有房子。即使春天来了,我们也看不到柳条和樱花。我们只能看到米库旁边的鲜红色山茶花和枸橘的淡绿色花蕾。
西侧有一空地,散落的石砖中间有一些紫云英和紫花地丁。我开始采摘紫云英取乐。摘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前几天隔壁一个小孩嘲笑我说:“没有男生摘花!”于是我赶紧四下看看,把花扔了。还好没看到。我只是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能听到妈妈织毛衣的声音。
空在这片土地的另一边有一个叫小源的家庭,那里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去她家玩,就绕着门跑了进去。
我脱下凉鞋,砰的一声打开滑动门,走了进去。发现阿姨在和一个不认识的女生看书。这个女孩穿着红色和服,头戴岛田发髻。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孩是城里人。姨妈和姑娘都惊讶地抬头看着我,脸涨得通红。虽然当时我还小,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表现有些不自然,而且平时也不一样。看着那本书,上面有漂亮的彩色图片。
“阿姨,那是图画书吗?”
我凑过来问。女孩把书翻过来,看着姑姑的脸笑了。我看到那本书的封面也是五颜六色的,大大的有一张女人的脸。
阿姨接过女孩的书,打开放在我面前,指着里面的图片问我:
“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女孩笑得越大声。我仔细看了看,画面上人物的姿势复杂到我看不懂。
“是脚吗?”
这次姨妈和姑娘一起笑了。好像不是一只脚。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嘲笑了。
“阿姨,我要走了。”
尽管阿姨叫我“等一下”,我还是跑出了大门。
以我当时的知识,我无法判断他们在看什么图片,但我知道他们的语言和动作都是不正常的,让我觉得不开心。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一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妈。
七岁。
父亲从东京回来了。我开始上学,学校是在前旧金山学习学院的旧址上建立的。
从家到学校,我要经过门前护城河最西端的大门。城门的岗哨保持原样,里面住着一位50岁的叔叔和他的妻子及孩子。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一个男孩子,总是穿着破衣服,两条鼻涕拖得很长。每次我经过那里,孩子总是用手指看着我。我带着厌恶和一些恐惧从他身边走过。
一天,当我走过城门时,我看不到那个总是站在外面的孩子。我正想着孩子怎么了,就在我要经过柱子前面的时候,房间里传来叔叔的声音:
“嘿!你要拿那个做什么!”
我停下来,朝声音的方向看去。大叔正盘腿坐着编织草鞋,刚才他在训斥孩子,因为他想拿出用来打草的木槌。孩子放下木槌看着我,大叔也看着我。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棕色的皱纹,鼻子又高又歪,脸很瘦。看到他的眼睛,白色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些发红和发黄。大叔对我说:
“孩子,你知道你爸爸和你妈妈晚上做什么吗?你只睡懒觉,我不知道。哈哈哈!”
他笑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也笑了。
我不理他就跑了。身后还能听到两个人的笑声。
我一直在想我叔叔刚才问的话。我知道男女结婚都会生孩子,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生孩子。大叔说的应该和这个有关。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
虽然我也想知道秘密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想到晚上醒来监视父母在做什么,就像我叔叔说的那样。大叔说,即使在我这样的孩子心里,似乎也觉得亵渎神明。就像有人叫你不脱鞋就打开竹帘进神社。我讨厌叔叔那样说。
后来每次走过城门都会想起。但是,孩子的注意力总是被各种新鲜事物吸引,想很久都不可能。回到家大概忘了。
【1】外路:即非常规的旁道。
[2]夏目的帮助:夏目·索塞基(1867-1916),近代日本著名作家。
[3]切萨雷·龙勃罗梭:意大利精神病学家,他将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犯罪学研究。
【4】龅牙龟:指偷窥女浴的变态男性。起源于明治时代,有个外号叫偷看惯犯,Kametaro。
[5]chugu る:“chuguる”的意思是龅牙,日语动词后缀“る”构成动词,意思是强奸和性侵犯。
[6]Cherchez la femme:意思是找出那个女人。当一个男人行为异常,很难解释原因时,就用这个表达来形容。
[7]中国:这里指日本的一个地区,位于本州西部。
[8]下关:日本是指以城堡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
十岁。
我父亲开始一点点教我英语。
我经常听到父母提到他们可能会搬到东京。说起这件事,我要是听,我妈总是叫我不要告诉别人。我爸说如果我去东京,不能什么都带。家里要挑拣东西,所以经常去仓库搞点名堂。大米堆放在仓库的下层,放衣服和杂物的箱子放在二楼。当我父亲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客人来的时候,他会立即停下来。
我问我妈为什么不能告诉别人。我妈说因为大家都想去东京,不好说。
有一天,趁父亲不在家,我上了仓库二楼看了看。我看到手套箱的盖子打开了,很多东西散落在周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总是放在壁龛里的盔甲盒因为某种原因被拿出来放在房间中央。盔甲和头盔,这种东西,大概从五年前征服常州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作用。我父亲可能想在拿出来之前把这个满是灰尘的东西送到旧货店。
我不小心打开了装甲箱的盖子,发现上面有一本书。打开一看,上面有美丽的彩色图片,上面画的男女姿势很奇怪。我记得这本书和我年轻时在小源阿姨家看到的相似。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比我看到书的时候多了,所以我理解的比那个时候多了很多。虽然米开朗基罗壁画中的人物也使用了大胆的透视画法,但这本书中的人物与那本书中的人物不同,他们的姿势也相当奇怪。孩子分不清手和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一次我能看清自己的手脚,也明白了之前一直想知道的秘密应该是这个。
发现很有意思,翻了几张里面的图。但是,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人物的行为与人的欲望有关。叔本华说,人类很难有意识地寻求拥有自己的孩子和繁衍后代。所以,大自然让这个过程伴随着快乐,变成了欲望。这种快感和欲望是大自然为人类繁衍设计的阴谋和诱饵。即使没有这种诱饵,也是下层生物不妨碍繁殖,是没有理性意识的生物。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像图中人物这样的行为是伴随着这个诱饵的。之所以一遍又一遍津津有味地看这些图片,是因为我只对未知的东西感兴趣,只是一种好奇和求知欲,这和当时小源阿姨家那个拿着岛田包子的女孩看的角度完全不同。
在反复看的过程中,我也有疑惑,就是画的是某个身体部位。年轻的时候,把不是脚的地方错当成脚是情有可原的。本来这种画在任何国家都有,但是把某个身体部位画的这么大,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日本浮世绘画家的发明。古希腊艺术家在塑造神的形状时,把额头做得很大,把下脸做得很小。因为额头是灵魂存在的地方,所以放大来突出。脸的下半部分,也就是嘴的周围,是用来咀嚼的上颚和牙齿,是下半部分,所以刻意缩小。如果放大这部分,看起来会像猿。坎贝尔[1]的下半身越来越小,胸部比腹部还大。腹部的位置类似于下颌和牙齿的位置,不需要解释,因为呼吸的作用优于饮食。此外,古代人并不认为胸部,或者更确切地说,心脏,起着血液循环的作用,而是与精神活动有关。日本浮世绘画家在创作这些画面时放大了某个身体部位,和放大额头、胸部是一个道理。这在当时的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中国有本书叫《肉蒲团》。书中写道,主人公魏觉得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很小,所以他到处去偷看别人的尿。当时看到有人在路边撒尿偷窥。当时市里没有路边厕所,大家都在路边解决。我发现每个人的位置都很小,所以判断画是骗人的。当时觉得自己好像有了很大的发现。
这是我看过那张奇怪的图片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另一个观察很难说,但为了体现真实性,我决定写下来。我从未见过女人身体的任何部分。当时市里没有公共澡堂。不管是在家洗澡还是住亲戚家的时候,我都是只脱衣服,帮我洗澡的人都是穿衣服的。而女人在路边不回应自然的召唤。真的没办法。
在学校里,男生和女生是分开教的,从来不一起玩。即使说话也会立刻被同龄人嘲笑,所以没有异性伴侣。亲戚中虽然有女生,但也只会在一些节日或者练功会上来。就算他们来了,也只会打扮打扮之后再来,然后老老实实的吃饭再走。没有女生能亲密无间的在一起玩。但是,我家后面住着一个当时叫侏儒的侏儒,那户人家有个女儿叫阿生,跟我同岁。阿生戴着一个小蝴蝶髻,偶尔来我家玩。她皮肤白皙,脸蛋鼓鼓的,性格很乖巧。不幸的是,她成了我的对象。
刚刚过完雨季。闷热的下午,妈妈还在织布,来我家帮忙干活的奶奶正在午睡。屋里静悄悄的,只有母亲织布机发出的梭子声在屋里回荡。
我一个人在后院的仓库前,用一根细线系着一只蜻蜓的尾巴,让它飞着玩。在满是红花的紫薇树上,一个禅来了,开始唱歌。我仔细找了一下,但是太高了,抓不住。正在这时,阿胜来了。她也是因为家里人在午睡无聊才跑出来的。
“我们一起玩吧。”
她向我打招呼。我突然有了一个计划。
“好吧,我们沿着走廊跳下去玩。”
我一边说,一边脱下凉鞋,爬进走廊。盛也跟着脱了红鞋带的草鞋。首先,我赤脚跳到院子里的青苔上,阿生跳了下来。我又爬进了走廊,这次我撩起了衣服。
“你这样跳下去,衣服不会碍事。”
我赶紧跳了下去。胜见,我很犹豫。
“快,你试试!”
阿生的脸上看起来很尴尬,但毕竟是个单纯温顺的孩子,最后还是撩起衣服跳了下来。我瞪着眼,除了两条白腿连着我的白肚皮,什么都没有。想想一位失望的绅士,他拿着望远镜在芭蕾舞演员的两腿之间窥视,却看到金色的丝绸在薄纱衣服上闪闪发光。我的行为无罪。
那年秋天。
在我们那里,保龄球非常受欢迎。就在农历的苯教节临近之际,有传言称今年不允许举办苯教舞。但出生在外国的县令认为违背当地人的意愿是不合适的,于是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态度。
离我家两三百米就是市场了,那里摆着摊。晚上可以听到伴奏。
我问我妈妈她是否能去参加舞会。我妈妈说她可以去,但她必须早点回来。于是我穿上凉鞋跑了出去。
其实之前看了很多次,不过那时候比较小,我妈带着看的。参加舞会的人表面上都是本地公民,但都是裹着头巾的脸,所以很多武士的孩子跳舞。其中有男扮女装的,也有女扮男装的。不戴头巾的人戴一个叫“百眼”的面具。西方的狂欢节在一月。虽然季节不同,但人们做类似的事情却步调一致。在西方,收获季节还有其他舞蹈,但好像不戴面具。
很多人围成一个圈跳。有些人戴着面具来,但只有袖手旁观和观看,这样一旦他们看到他们喜欢的舞者,他们就可以随时插入他们。
我正看着,无意中听到两个蒙面人的对话,好像认识。
“你昨晚去了阿塔戈山。”
“别瞎说!”
“不,我一定是走了。”
这时,另一个人从旁边插话道:
“那个地方,早上去看看,还有很多东西没带走。”
然后就是笑声。我突然觉得好像摸到了什么脏东西。我不再看球,跑回家。
[1]坎波:希腊神话的女妖,长着女人的躯干、头和像蝎子一样的尾巴。

1.《森鸥外 森鸥外:情欲生活(一)》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森鸥外 森鸥外:情欲生活(一)》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nei/1652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