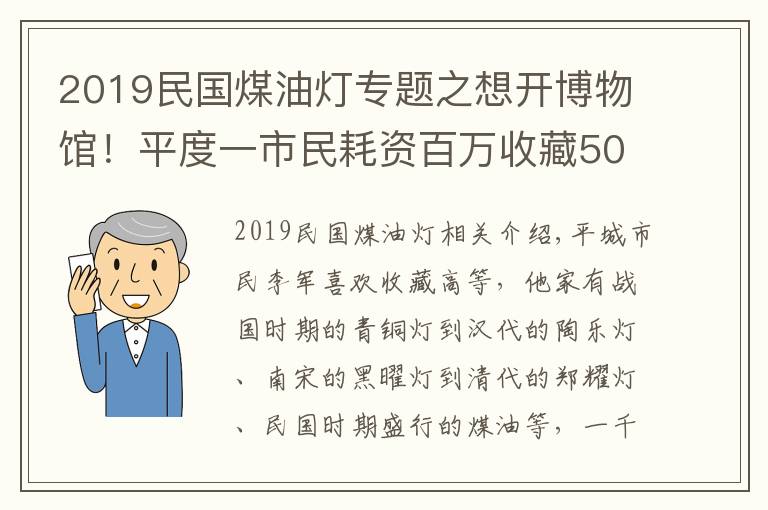于文谦在榆木文学中创作
我是刘沙县北寨乡北寨村的苏怡教,1963年2月出生。
在我童年阶段的近三千个夜晚,是在煤油灯下度过的。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农业学大寨”,全民“学雷锋”运动。1966年又开展了为时十年的“文革”运动。那时,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种田靠的是牛,拉东西靠的是骡、马、驴等牲畜,出行靠的是步行或胶皮车,加工粮食用的是石碾、石磨或水磨,穿衣靠的是婆婆与妈妈老一辈自纺自织自做的粗布衣服,黑夜靠的是煤油灯照明。
大约七十年代初,北寨公社才有了拖拉机,一部分平地才实现了机耕,各大队也才有了电磨,出现了历史性的的转折与变化,大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那时,虽然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水平比战争年代好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但我国的国民经济还正处在恢复阶段,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落后。那时,社员们住的都是土木结构的四檩房,一丈一尺长的大梁,七尺长的檩子,屋子空间非常窄狭,一家七、八口人挤在一盘小炕上,还有的社员仍住在土窑洞里。当时,房子的墙壁全部是用泥摸下的,经济条件好点的户用石灰水等涂料粉刷一下,有的户连石灰也买不起,只能是泥墙。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夜里点着煤油灯,黑烟不停地冒着,天长日久整个屋子都被熏得黑乎乎的。有的户一年粉刷一次,有的户几年才粉刷一次,大多数户粉刷不起,只能将就住。那时,谁还能顾得上煤烟污染,小小的煤油灯在漫漫长夜里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馨,带来了乐趣,也带来了希望。
摄影|张云
在煤油灯下,自己与姐、哥、姊妹们经常用手变兔子,变其它图形,寻找乐趣;在摇曳的灯光下,婆婆或妈妈有时织布,有时纳鞋底子,有时洗锅刷碗或做其它针线活。父亲在灯光下记账或聊天。兄弟姐妹们大部分时间学习,有时也听大人们聊天。
我记得婆婆很会讲“黑瞎话”,在煤油灯下,婆婆有时讲战争年代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有时讲她听别人说过的真人真事或神话传说,语言朴素,绘声绘色,形象深动,我非常爱听。在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我们无不义愤填膺,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恨不能与日本侵略者拼个你死我活,只可惜不在那个时代。据婆婆讲,那时村民们在山里都打着躲难窑,一听说日本兵来了,就赶紧拉上牲口,担上锅碗勺筷往躲难窑里跑。可也有跑不掉的时候。
194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爷爷与婆婆正坐在炕上就着白萝卜咸菜吃米汤煮疙瘩,或听街上有人吆喊“日本人来了,快跑!”爷爷与婆婆赶紧下地出门拉上牲口就跑,还未跑出街门,就听见鬼子“呜哩哇啦”一正乱叫,爷爷赶紧将婆婆推到牲口棚里躲起来,他自己却被鬼子抓住带往辽州修公路。不过,在去辽州的途中,爷爷借口方便,冒着生命危险,乘鬼子不注意跑掉了。那次,日本人在北寨村杀了很多人。牛旭珍爷爷家除了牛宪忠二大爷外,好几口人在四引沟一个土窑洞里全被鬼子活活烧死了,连其他亲戚一共烧死八个人,其状惨不忍睹。听到此,我们的牙齿咬得圪蹦蹦响,恨不能剥了日本鬼子的皮,抽了日本鬼子的筋。此时,小小的煤油灯照着我们仇恨的脸,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在煤油灯下,我从当时的缺吃少穿联想到以后怎样才能丰衣足食;从眼前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联想到我国甚时才能实现自动化、现代化;甚时才能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使人们从按劳分配的体制发展到按需分配的高级境界中。
1971年,北寨村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线。1972年秋天,我村往下至青峪各村正式通了电。
刚通电的那天夜里,我望着光芒四射的电灯与白天般一样明朗的屋子,心里充满了惊奇与喜悦,心想,这一下可好了,在亮堂堂的屋子里无论是做家务还是看书学习,干什么都方便了。我从煤油灯到电灯神奇而伟大的变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与变化,心中充满了对共和国与共产党的热爱,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遐想与希望。
李长茂:记忆中的油灯变革史
偶然看到一幅画面——《麻油灯下》,一下子勾起了心底尘封的记忆。画面上的夜,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在土炕上的一盏油灯划破了黑暗。麻油灯早年是用生铁铸的底盘,中间似麻花的细熟铁棍,上面铸个像小碟儿似的油盘盛油。这种用具是从古老流传下来的。后来改制为下面是一小方块木座,中间是一根圆形木棍。上面插一个灯台的,有铁皮的、有锡制的、也有少数是铜制的。用手搓一支棉花灯芯,里面倒上麻油,随时左右摇曳火苗。人们,特别是小孩一不小心,把炕上的油灯打翻,到处都是油,让人很烦恼。但也有无油人家,把大麻除皮,用高粱杆皮或用细铁丝将十几个除皮的大麻串连在一起,点火照明。孩子们用它写字、看书。
灯边围着的人,在灯光的照映下,有了层次感,放映在墙上,看起来如同幻灯一般,大人们用手变各种动作逗着孩子玩。女人们在灯下低头默默地纳鞋帮、绱鞋、缝补衣裳。大人小孩争着这灯光。大一些的孩子抱着小弟、小妹看大人做活,还是坐在较远的地方。光照不到是模糊的,在忽明忽暗的光彩中带来了家庭的气氛,麻油灯下唯一的效果就是静。这种朦胧的光彩,如抒情曲伴着孤独和忧伤,是夜的曼妙背景。在古时,夜间唱戏也是使用麻油灯照明。它是做个三角铁架、上面放个铁盆、用棉花搓三支一寸粗的灯芯,里面放上油吊在空中,随时左右摇曳火苗,但光照还很阴暗。
再后来“洋油”进入中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美浮鹰牌”煤油成了抢手货,价格很贵,一些富裕人家开始使用煤油点灯。灯壶是圆形而扁,中间有个小圆口,上面加个盖中间有根黄豆粗的空心细管,里面用棉线或纸做个灯芯,里面放上煤油,把油壶放在早年使用的灯台上,它是用铁皮或铜制的。
那时,煤油灯光线很亮,但也很厌烦,甚至有些恨。只要一时不注意鼻孔出气大一点儿或有点风,灯就被熄灭。并有顺口溜:“煤油灯省油不省洋曲灯(火柴)”。突然一阵子,油灯的火苗会息闭的,眼前景物也变得一明一暗,似乎在抖动。大人们着手调整灯芯子,轻轻地拧着。调好了一切恢复平静,灯又稳稳地罩住这个小小世界。从窗子向外望,邻居的家里也亮着煤油灯,知道那家的大人也在做针线活,孩子们也在学习,那里也有个小小的世界。那时候,煤油灯光似乎特别柔和了,如同自己湿润轻盈的心境。后来由大城市传入汽灯,在大场合或夜晚唱戏使用汽灯照明,那就很时髦了,光线亮的很扎眼。
在解放前商号、公众场地;以及解放后集体单位机关、包括农业社,都各有玻璃制的灯台和灯罩,灯台也有马铁口皮或铜制的,灯台上还有个铁皮灯口,上面有三个爪,中间有支横杆控制火苗大小,灯芯是用棉线织成的。这样灯人称“美浮灯”。点灯时,拿下灯罩,把灯罩用布擦得光光亮亮,用火柴点火,刚开始火苗蹿老高,冒着黑烟,左右摇曳。加上灯罩火苗就收小了,变成一小粒,光也亮多了。在1959年通电后逐渐淘汰。由于电力不足经常停电,还备此灯,放在窗台上随时取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到八十年代彻底淘汰。如今,当年的油灯就躲藏在记忆的角落里,无声无息,不经意间。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玻璃灯台和马灯。你如果用心地擦拭一下那被岁月之尘蒙蔽的灯罩,它会渐渐地亮起来,与之相伴的,是旧日那平凡难忘的时光。
史忠华:情系煤油灯
如水的光阴,如水的岁月。记忆中那盏如豆的油灯,犹一艘搁浅的小船,在时光的长河里摇曳,那一抹抹心底的温柔,也软软的随波荡漾开来……
据母亲讲,1964年1月20日,正值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季节。萧瑟的冬日,瘠薄的年月,农村的午夜传来了新生儿的啼哭声,一个骨瘦如柴的我,降生到了农家大院的一盘土炕上,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除了生我的母亲,邻居接生的奶奶,就是一盏或明或暗,火苗跳跃的煤油灯了。
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农家,日子过得像力尽的老牛,残喘着。
一周没有吃过一口奶水的我,只靠喝点清米汤,哭声连刚出生的小猫高也没有。“这是一条命呢,送人吧,要不就活活饿死了”,父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接生的奶奶过来劝母亲“你不想想,你们家人多,她现在还小,吃穿花不了太多,起码你们家能多分一个人的口粮,多领一个人的布票”。长我12岁的哥哥,更是一跳三尺高“不能送人,没听说把自己孩子送人的”。母亲满脸的无奈,面对穷的像一张A4纸苍白瘦薄的家,喃喃道“怎么办?一口奶也没有,家里也没钱买奶粉、麦乳精呀,总不能天天喝米汤吧!”接生奶奶出主意“就喂点白面糊糊吧”。哥哥仿佛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妈妈你做好,我来喂”。于是,母亲做好面糊糊,在筷子的一头缠上棉花,用白色细线把棉花捆紧,然后用有棉花的一头蘸上稀稀的面糊,喂到我的口里。白天有阳光的眷顾,一切看得清楚,自然是好的。夜晚,昏暗的油灯下,12岁的哥哥抱着刚刚满月的我,蘸着面糊糊,精心的喂着,可能是我太饿了,用力一吮吸,就将面糊连同棉花吸进去,卡在喉咙里,小脸憋得通红,咳嗽不止,哥哥、母亲吓坏了,连忙拍着我的背,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农家的孩子,就如大田里的草,给点阳光就灿烂,淋点雨水就疯长。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点白面糊糊的喂养,一盏不灭的油灯陪伴,一缕亲情的呵护,我开始咿呀学语,开始蹒跚走路,尽管营养不良,尽管面黄肌瘦,但也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有了思维,有了记忆。
而在记忆深处,那如荧的煤油灯,永远跳跃在农村漆黑的夜晚,远逝的岁月,也深藏在那橘黄色的背景之中,给农家涂上了昏黄神秘的颜色,也给我的童年开启了一道生命的霞光。
夕阳退去,天空立马拉下黑色的幕帘。家中一盏煤油灯,发着微弱的光芒,这是一盏铁质的油灯,中间一根不到一尺长的细铁棍直直相连着上下两个盘子,下面的底盘,是为了保持油灯的稳固,上面的托盘盛放煤油,一根用棉线搓成的灯捻子放在煤油里,灯捻的一端稍露在托盘外面,被火点燃,整个屋子被它摇曳的朦朦胧胧,妈妈和大姐在灯下缝缝补补,父亲在地上掰着玉米棒,二姐借着瘦弱的灯影,通过手势的变化,在屋子的土墙上,为我们创造出种种形象。只见她只需一只手,将拇指食指一捏,其它三个手指伸直,土墙是就是一只骄傲的孔雀;两拇指十字相挨,一只手四指稍弯曲,另一只手四指伸展,就是一只飞翔的老鹰。二姐的两只手缠绕勾连,不停的变换,时而是一只蹲着、卧着的安详的兔子,时而就又成了一只奔跑的骏马。二哥写完作业也加入进来,墙上的手影变的更加生动,有趣,二哥的“老狼”,在咬二姐的“狗”,二姐的“狗”嗡嗡吠叫,腾、挪、躲、闪,二哥的“狼”,穷追猛打,狂咬不止,我和弟弟边看边叫,“往右,掉头,快跑”,几个回合下来,“狼”终究吞噬了“狗”……煤油灯下,使清汤寡水的童年变得有滋有味,也使枯燥乏味的童年变得有了色彩。
日子,就像串起的珠子,而每年的腊月初一,就如一颗七彩的玛瑙。在乡间有这样一句俗语“腊月初一不吃炒,这个起来那个倒”。也就是说,腊月初一一定要吃炒豆子,把一年的灾难病痛像嚼豆子一样咬碎,准备迎接新的一年。而腊月初一吃炒豆也是有讲究的,初一一早睁开眼,不许说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吃三颗炒豆子。所以,初一的前一天,母亲就先选好黄豆,把个大、饱满、圆润的黄豆,用温水加点盐泡好,等到膨大后捞出,再端到寒冷的院子里冻上。等到晚上,母亲把油灯里添上满满的煤油,再换一根较粗的灯捻,为了使灯照的亮,照的远,特意在靠近灶火的炕上放一高凳,新拾掇的油灯,放在凳子上面,照的满屋生辉,也映的我们眼里发光,点亮的煤油灯,如进军的号角,拉开炒豆的帷幕。父亲是我们家的炒豆高手,首先,父亲让我们抱来早就准备好的芝麻杆、茄苗杆,放进灶火口点燃,一口大铁锅里面,盛着父亲找来的粗沙,铁锅严严的放在灶火上,待铁锅烧热,改为小火,父亲将锅里的粗沙,拿一根棍子不停的搅动,等沙受热均匀,再把豆子倒入锅中,继续把豆子和沙子不停的搅,这时一定要掌控好火候。火太大,炒出的豆子会黑会苦,品相不好,口感不行,小火炒出的豆子,发蔫,没有脆感。一定要中火炒制,噼噼啪啪的声音,炸成一簇簇霍霍燃烧的火焰,将锅底烧的通红,也将灶台旁忙碌的父亲的脸映的彤红,锅里的热气,屋里的烟气,腾腾的冒着,蒸腾出一种生活的气息。炒好一锅后,父亲把粗沙和豆子一起倒入筛子里,粗沙随着筛子的摇动,顺着窟窿眼溜下去,筛子里留下的是酥、脆、香的豆子。橘黄色的煤油灯,红色的灶火,照的屋子亮亮的,暖暖的,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的是炒黄豆的香味。
嚼着喷香的炒豆,一场物质盛宴刚刚闭幕,精神盛宴便粉墨登场。尽管母亲大字不识,父亲也只上过四年学堂,但每晚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自从哥哥能识文断字后,就成了家里雷打不动的规定。煤油灯下,上五年级的姐姐,继续着昨天的故事,一家人静静的聆听,连调皮的小猫也慵懒的躺在暖暖的灶台上。.屋子里,油灯下,只剩下母亲纳鞋帮的声音和姐姐读《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声音。多少个这样的冬日,多少个这样的场景,先后听了哥哥姐姐读的《水浒传》、《烈火金刚》、《青春之歌》、《三国演义》、《李自成》等。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就是《李自成》一书中,对义女慧梅的描写,特佩服她内柔外刚、侠肝义胆的品质,以至于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
腊月里,煤油灯下剪窗花,也成了每个女孩的必修课。首先找来窗花纸样,贴于要复制的白纸上,白纸与纸样放整齐,纸样的一面对着煤油灯上方慢慢进行烟熏,这是一个细致活,不得移动白纸和纸样,一定要熏的均匀,纸样上的叶呀、草呀、花呀、果呀细细的,密密的才可重现在白纸上,去掉被烟熏黑的纸样,白纸上就留下清晰的底样,这时方可将红纸与底样用针线粗略的缝制在一起,按照熏制好的花形,修剪窗花了。一到过年,家家窗户纸上,贴着,什么喜鹊登梅、福字、柿子如意、鱼跃龙门等等寓意吉祥的窗花。静谧的夜晚,橘黄色的油灯,雪白的窗户纸,大红的窗花,为农家添上了节日的喜气,给单调的日子填补上了美轮美奂的色彩。
渐渐的,我也欣喜的背起书包,进了学校,可以自己读书学习了,油灯下,写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本本黑白小人书,就成了我爱不释手的伙伴,《鸡毛信》、《小兵张嘎》、《鲁智深痛打镇关西》、《小英雄雨来》等开启了我的心智,树立起善恶评判的标准。
漫长的冬夜,窗外北风呼啸,屋里的煤火已封,伴随油灯捻子的噼啪声,有时半夜醒来,看到调暗的油灯下,母亲在飞针走线。我们懂得母亲调暗灯光的用意,一是怕影响我们休息,二是当时煤油紧俏,需凭票购买。看到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左手握鞋底,右手拿锥子,扎孔,穿针、引线,再用力把麻绳缠在右手掌拉紧,尽管右手中指戴着顶针,手掌上戴着手隔套,但也可看到母亲手上有麻绳勒的印痕。麻绳在摇曳的灯光下,随着小小的银针一闪一闪,针与线不停的在鞋底的两面,穿来穿去,发出嗖嗖声响,每纳三四道,母亲就在头发上擦一下针。多少个春夏秋冬,煤油灯下,母亲一直在织呀,纳呀,补呀,洗呀,辛劳和疲倦织进了她的额头眼角,母亲用自己的黑发、银丝缝制希望,把幸福喜悦纳成对子女的期待,用她的不眠不休,缝补家境的窘迫,浆洗贫穷的生活。油灯下,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父母的不易。
油灯星星点点,飘飘闪闪,织起生活的经,编成经历的纬。70年代末的农村虽已通电,但一到晚上就会停电,依然漆黑一片。恢复高考后,学校加上晚自习,煤油灯就成了我们不可忽缺的照明工具,于是兴起一股自制煤油灯的热潮。
找一个装过西药的小玻璃瓶或墨水瓶,里面倒上煤油,再找一个铁片,或铁盖,在盖中间打一小孔,在孔中间穿一个用铁片卷成的小筒,再用棉线,搓成细捻穿到孔里,上端露出少许,把较长的下端泡到煤油里,拧紧瓶盖,油灯就做好了。
50多个人的教室,50多盏自制煤油灯,放在课桌的一角,点燃的油灯,将教室照的充满生机。教室门窗紧闭,就连走动也不敢快,因为油灯火苗太脆弱了,经不住一点风的吹拂,霍霍点燃的火苗下,是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有的背语文,有的解数学,有的做物理,有的互相讨论……两个小时的晚自习,鼻孔、眼窝都被油灯給熏黑了,用手一抹,嘴唇上会留下一二道黑印,有搞恶作剧的男生,偷偷的把女生的发梢放到火苗上燎,直到闻到焦糊的味儿时,方能察觉。如豆的灯,如荧的火,点燃起学习的热情,也燃成了那个时代校园特有的风景,跳出农门,远离黄土,成了我们读书的动力,天空的星星与教室的油灯相映衬,高悬的明月见证了夜晚油灯闪烁的校园,见证了油灯下莘莘学子苦读的身影……
如果不曾有油灯的光,我不知道什么是亮,如果不曾有油灯的伴随,我不知道什么是成长。如今,过去的石头盖成了楼,曾经的高山变成了丘。记忆中的油灯,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华丽的电灯,取代了油灯的前世,化作了美丽的今生。而记忆中的那盏油灯,却将永远闪亮在心灵的深处,熠熠生辉,不灭不熄!
张宁静:儿时煤油灯的往事
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我已走近古稀之年。进入老年后,经常是“近事不记,往事记。”思想心灵回忆,老往岁月深处走;那些难忘的旧时生活片段,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充满了甜蜜的趣味和愉快的回忆。
儿时的一盏煤油灯便把我拉回到那个时代。我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成立;百废待兴。那时的榆次城内居民基本上还没有通电。每当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便点燃了煤油灯照明。就是这一盏盏大大小小的煤油灯,抖动着的小火苗让每家每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活跃起来……
当年,我家住在榆次阁北街17号两间民宅。每天傍晚,天色便渐渐暗了下来了,母亲拿一根火柴划着点燃煤油灯后,再用针挑一下灯芯,煤油灯便发出了昏黄的光,窄小的屋内便有了些亮光。
煤油灯的制作很简单,用一个旧瓶子,在瓶盖中间插上一根细长的园铁皮管,管内放入一根长度适中的棉花芯,把从五交化商店买回来的煤油倒入瓶内,一个很简单的煤油灯便制做成功了。
我依然记得:每天晚上,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着做着家务,也就把当时那枯燥的时光变的快乐有趣。每当我放学回到家,母亲便把煤油灯移到我写作业的方桌上,并用针挑一下灯芯,煤油灯也就更亮了些,以便我写作业;有时,不注意,一阵风吹来,煤油灯熄灭了,屋内马上漆黑一团,这时,母亲让我不要动,找来火柴划着后点着煤油灯,屋内就又亮起来了。我在煤油灯跳动的火苗下,赶紧把作业写完好早睡觉。夜间我有时醒来把便,看见母亲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制衣服,我便说:“妈,不早了,快睡觉吧!”母亲朝我微微一笑说:“你先睡吧!我再赶制一会儿,好让你们过年穿上新衣服!”
还有一件至今难以忘却的往事。有一天夜里,我起来把便,叫醒母亲点灯,母亲从睡意中醒来,划着火柴,点着灯后,顺手将火柴扔到地上,不巧,正好扔在哥的鞋里。由于余火未灭,将一只鞋烧毁。全家人都在睡觉,谁也没有发现。后半夜被烟熏醒才发现一只鞋已烧毁。哥没鞋穿了,不能上学了。母亲十分着急,去学校给哥请了两天假。连明彻夜才赶制出一双新鞋,哥穿上后才去上学。现在回忆起来实在令人好笑……
那时的煤油由于质量差,每天早晨起来,鼻孔里全是黑的,都是被煤油灯烟熏的。
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如遇晚上没事,为了节约,母亲便吹灭煤油灯让我们早早睡觉,睡下后听母亲给我们讲故事,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
尽管那时的生活虽然简朴,但煤油灯下的日子却充满着无尽的甜蜜和欢乐。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质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电灯、空调、手机、电脑闯进了百姓的生活。城市变得五光十色,亮丽的灯光又把城市装潢的五彩缤纷。陪伴我度过儿时的煤油灯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去不复还了,但却留在了人们永远的历史记忆中。
围灯———太谷人久远的记忆
围灯,也称马灯,咱太谷人习惯称之为围灯,是一种烧煤油的灯,可以用手提着,也可以挂在墙上、树上,有防风雨的功能。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设计非常实用、精巧的灯给生活在农村的人们送去了温暖的光芒,成为那个时代太谷人抹不去的记忆。
记忆中,围灯中间部位安置有玻璃灯罩,灯罩用铁丝固定,下边是装煤油的圆形盒子。小时候,农村经常停电,一般人家都是用煤油灯,围灯很少用,那时谁家要是有一盏围灯,会让很多人羡慕的。生产队饲养牲口的马厩里就挂着好几盏围灯,负责喂养牲口的是一位名叫二娃的大爷,由于是我家的邻居,平日里,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他看管的马厩里玩耍或者掏鸟窝,所以,我对围灯有着非常特别的记忆。马厩里的光线并不好,尤其是阴雨天,二娃大爷都会用手把围灯下面的一个小钮调一调,顿时,屋子里亮堂起来,勤劳的二娃大爷用柳条编制的大簸箕装满粉碎的玉米秆,在围灯下给马或驴添草料。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一到夜晚,村里村外一片漆黑,大人们怕娃娃们害怕,纷纷点起围灯,任凭调皮的娃娃们到处追逐打闹,自己早早地躺到土坑上抽着旱烟,大口大口地吐着烟雾,呛得老人和娃娃们一个劲地咳嗽。那个时候,村里人的生活真的惶,家庭富裕点的城里人,家里差不多都有台收音机,而村里的人家搜遍全部家当最多也是只有个手电。
二娃大爷家的四儿子在城里做小买卖,以卖豆腐为生。记得有一年四儿子给他老爹花9块钱买了一个半导体,从那个时候起,大人娃娃晚上有事没事都争着抢着往马厩开跑,为的是挤在那里蹲在围灯下面可以听广播。那时候,村里经常会有人家要翻盖房子,旧房子拆掉没有地方住,于是,夜里就没了全家人睡觉的地方,每每这个时候,大人们就会在院子里搭个简易帐篷,之后,在帐篷里的柱子上钉个钉子,把围灯挂在上面,在围灯下,一家人要度过几个月的时间。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个说法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听到的,也是当时农村普遍有了照明灯的真实写照。从那时起,村里基本上都通了电,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围灯从那个时候就很少有人家使用了。
榆次五十年代中期通了电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住在矮小阴暗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用煤油灯照明。母亲每天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每想起来,都会使我的眼睛淌出泪花,难以忘怀!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通了电,家里安装了电灯,屋里一下亮堂起来。电灯的逐步普及,使人们的生活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起初的电灯用的灯泡是白炽灯,牌子记得是“光明”牌和“亚”字牌,其它的牌子印象不深,后来又出现了日光灯。据说,25瓦的日光灯可抵上100瓦左右的白炽灯!因这种灯比较贵,所以用的家庭很少。那时,电灯的灯泡分螺口和卡口,而螺口居多。现在,卡口一般没有了,而螺口却一统天下了。
电灯,不管是螺口还是卡口的白炽灯都是用钨丝元件制作的,灯泡里抽掉空气成真空,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灯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钨丝烧断了,俗称“灯泡吹了”。一些懂技术的人们便想出办法,利用“搭丝”的办法连接起来还可以再使用一段,“搭丝”是短路,比以前稍亮些,但由于温度高,所以寿命较短烧得时间长了就又断了。
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各种商品是凭票供应,而电灯泡更是紧缺,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人们往往通过“走后门”、“找关系”购买。当时商店规定买一个灯泡需要回收一个坏灯泡,翻新后能重新使用。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省电,一般家庭用的都是40瓦以下的灯泡,记得40瓦的灯泡是3角5分钱,还常常缺货。
更让人们担心的是由于技术问题,灯泡里真空抽得不净等原因,经常会发生灯泡突然爆炸。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电灯泡的稳定性、安全性也大幅度提高。21世纪初,随着新型节能灯的普及,与普通白炽灯相比节能提高了90%,还又环保。使“电灯”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电灯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图为七十年代的购灯凭证。
榆次,电灯的往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迅猛发展,人们陆续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经过人们精心的装潢,客厅天华板上的灯光五光十色,更使家里显得高雅、温馨。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大家面前。
看着明亮多彩的灯光,不免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住在矮小阴暗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用煤油灯照明。母亲每天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每想起来,都会使我的眼睛淌出泪花,难以忘怀!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通了电,家里安装了电灯,屋里显然亮堂起来。电灯的逐步普及,使人们的生活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起初的电灯用的灯泡是白炽灯,牌子记得是“光明”牌和“亚”字牌,其它的牌子印象不深,后来又出现了日光灯。据说,25瓦的日光灯可抵上100瓦左右的白炽灯!因这种灯比较贵,所以用的家庭很少。那时,电灯的灯泡分螺口和卡口,而螺口用居多。现在,卡口一般没有了,而螺口却一统天下了。
电灯,不管是螺口还是卡口的白炽灯都是用钨丝元件制作的,灯泡里抽掉空气成真空,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灯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钨丝烧断了,俗称“灯泡吹了”。一些懂技术的人们便想出办法,利用“搭丝”的办法连接起来还可以再使用一段,“搭丝”是短路,比以前稍亮些,但由于温度高,所以寿命较短烧得时间长了就又断了。
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各种商品是凭票供应,而电灯泡更是紧缺,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人们往往通过“走后门”、“找关系”购买。当时商店规定买一个灯泡须要回收一个坏灯泡,翻新后能重新使用。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省电,一般家庭用的都是40瓦以下的灯泡,记得40瓦的灯光是3角5分钱,还常常缺货。
更让人们担心的事是由于技术问题,灯泡里真空抽得不净等原因,经常会发生灯泡突然爆炸。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电灯泡的稳定性,安全性也大幅度提高。21世纪初,随着新型节能灯的普及,与普通白炽灯相比节能提高了90%,还又环保。使“电灯”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电灯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阎锡山吞并魏榆电灯公司始末
榆次魏榆电灯公司创建于1924年,它是山西省电气行业创先者之一,当时全省仅有太原创建了新建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建立给榆次发展近代工业开辟了新的道路,打下了新的动力基础,也为榆次人民照明带来了福音。从此,电灯取代了油灯,开始结束榆次几千年点油灯的历史。
民国13年(1924年),由宋纯如、张权三等邑绅,以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集资五万银元,在榆次城北关购买土地四亩,建筑厂房五十余间,购置主要设备十余台,其中有蒸汽引擎两部,德国西门子一百马力三相交流电发电机一部,锅炉一台等。经过一年多筹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六月正式投产输电。该公司由宋纯如任经理,张叔三任副经理,招用工人三十五人,日产电二十余万度。当时发电量虽然很小,但也基本上能供足商号、机关、少数住户及一些工厂动力用电。
经历四年后,由于生产不断发展,需电量逐步增长,于1929年5月间,添购了德国产的二百三十马力交流发电机一部,锅炉一台等设备,从而增大了发电量。这时的发电量为四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三度,基本上适应了本地的生产和照明需要,由于经营妥善,又是都行业务,因此,获利较多。
鉴于机器设备磨损数年,需要更新修理,于1931年续资五万元进行了设备更新,主要添置了邦甫三架,二百开升压一具等,并架设线路十二公里。从此,该公司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发电厂,总容量为一百九十六基罗瓦特,总发电量为四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三度,日用电为五万一千一百二十度,公用电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度,出售电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七十七度,用户共计六百九十三户,其中工厂三户,商店四百六十七户,住户一百七十四户,机关四十九户,年营业收入四万六千九百九十九元,除设备维修和线路修理,工人工资及其它开支外,净可盈利万余元。
1932年,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以大兴实业为名,筹建了山西西北实业公司,于1933年八月一日成立。用这个招牌来排挤和吞并民族资本家的私营工业,魏榆电灯公司就是以名为租赁实为掠夺的幌子,收归西北实业公司管理的。以后,该公司逐渐衰退,一年不如一年。1934年仅发电三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度,比收归西北实业公司前降低了百分之十以上。
1937年,日寇侵占榆次时,处于停产状态,后由日寇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并派日军监视,强迫恢复生产。这时的公司规模很小,仅有工人十五人,发电量仅达一万余度,实际仅供日寇使用。因为日寇用电不出钱少出钱,已形成了亏损局面。
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重返太原,魏榆电灯公司仍归西北实业公司所管。这时,由于设备多年不更新维修,加上日寇破坏,虽然维持生产,但已破烂不堪,发电量很小,所以亏损较大。1948年榆次解放后,由华北实业公司接收,后移交榆次邮电局接管,由于无发展的必要,随后关闭停产。
张宁静
平遥近代电力与面粉工业
郝 亮
民国12年(1923年),本县仕宦后代祁敬斋(本名福曾,又名曾福,祖籍山西高平孝义村人,曾祖祁贡曾任广东、广西巡抚,两广总督),联合乡绅赵鸿猷等人,集资20万元,在县城南门外西侧创办了股份制“金井电灯公司”,祁敬斋出任经理。购置安装了德国产直流蒸汽发电机一台,功率70千瓦,架设通县城主要商业街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衙门街、城隍庙街,为低压木杆铜导线,电网数公里长。1924年正式供电,主要用户是政府办公机构、较大的商铺、乡绅大户,都是照明用电。后因经营管理不善,设备发生故障运行不稳定,又发生水淹,1930年前后不能维持而停业。这是平遥电力工业的起始和先导,开电力行业之先河。定时鸣汽笛为号送电灯照明,曾引发居民们轰动性观赏,成为平遥一景,不少年长者至今犹记。
民国19年(1930年),平遥人王汝恩联合恒升庆经理杨汝霖(本县曹村人,著名商人杨绶、著名肺科专家杨铎之父)以及邵育进、杨林胜、祁敬斋共同出资10多万元(另据杨汝霖长子杨绶提供,出资人为恒升庆、兴隆信、永亨、丰发祥、永盛庆、复兴公、厚德恒、崇丰厚等九家银号、钱庄的东家共同出资)。在东大街板门底西侧炭市街(现二针)创办了“晋生面粉公司”,王汝恩出任经理,杨汝霖担任董事长。公司初建时安装了3台磨面机,以柴油机直接带动,安装10余千瓦小型发电机一台供厂内生产照明。民国23年(1934)工厂扩建,购置德国长城洋行的201马力煤汽机带128千瓦交流发电机,磨面机改由电动机带动,兼营平遥县城供电服务。白天供面粉生产用电,夜晚以鸣笛为号,向政府机关、商业街道、店铺、大户输送照明用电。于民国23年(1934年)中秋节开始送电,将“晋生面粉公司”易名为“晋生面粉电灯公司”。据1938年由侵华日军第二十师团编写出版的《山西大观?平遥》记述:“该厂为平遥最大的工厂,所产面粉除供应本县外,还大量销往外地,资本10万元,年产值3.822万元。”汽笛响,电灯亮,成为平遥县城一大新的风景。至此,金井电灯公司停业后,平遥县又恢复了比较正常的电力供应, 有用电者72户。不久,对外供电也有了动力用电,如泉福永(股东杨林胜独资)、合生泉(经理王汝恩独资)等面店的生产动力也用上了电力。
民国25年(1936年),晋生面粉电灯公司被统入山西官僚资本“西北实业公司”,改称平遥面粉发电厂,组织机构无大的变化,王汝恩仍担任经理。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侵占平遥,平遥面粉发电厂被劫取,改称“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平遥面粉厂”,番号为军管三三工厂,日本华北电业株式会社建制,由日本人米木拉山(又称毛里山)任经理,原经理王汝恩改为名誉经理,生产面粉为其侵华战争服务。民国30年(1941年)左右,低压线路延伸到西门外平遥火车站,火车站始有电力供应。当年春天,面粉升降机故障引发火灾,日寇抓捕七八人严刑拷打追查无结果。民国31年(1942)日本人改换经理为上野义男,一直到民国34年(1945)日寇投降。其间民国32年(1943年)春,发生201马力煤汽机断轴事故,日寇抓捕发电工人王杰、张兴胜、王庆兴、王子山、雷同吾、贺功等七人被严刑拷打、关押,因查不出什么,诬为共产党破坏,惨忍地将七人杀害于县城南门外,砍头抛入枯井。201马力德国产煤汽机断轴后,由新绛纱厂调来100马力煤汽机替换,并随机调来韩俊德、王顺等技术工人,又曾购置两台变压器改善电压,但小马拉大车效果一直不好,电压经常偏低,201马力煤汽机断轴后屡修不好。
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国民党阎锡山方面接管了平遥,平遥面粉发电厂又被其“西北实业公司”接受。公司派来了张则俊担任厂长,接管人员有:厂长事务,许子亮;工务科,韩俊德、王顺、路春高、路春义;业务科,关子平;总务,张喜东。时间不长,改由许子亮接任厂长,一直到民国37年(1948)7月平遥解放。
民国37年(1948)平遥解放,该厂作为官僚资本,共产党方面的“太行实业公司”从长治派来智风、郝兴斋、李玺接管了厂务,智风任经理,郝兴斋任支书负责工会、李玺负责生产,员工有80余名。1949年仅有电表20多个。
1953年5月13日,面粉生产线失火,厂房被大火烧坏,将机器调往大同,只留下发电供电工段30余人,成为专业的发电厂。供电范围仅供县城机关、商店、学校、医院、居民照明用电和西大街玉记铁工厂、城外火车站、及国营粮食加工厂动力用电,规模没有大的变化。平遥晋生面粉电灯公司从创办起,一直以县城为供电服务范围,发电设备一直维持民国23年(1934)安装的201马力煤汽机带128千瓦发电机的水平,低压电网以城内“干”字形主要商业街电网干线供电,用户除政府机关、商业店铺、乡绅大户、财东掌柜富户外,一般居民很少有用得起电灯的,所以电网范围一直很局限,发电和电网经营归当时的面粉发电厂,职工在100名左右,日伪和面粉实业公司时期大体维持这个水平。工厂管理除厂长外,设有工务(生产)、业务(供纺、财务、电费)及总务(包括保卫)。设生产面粉、发电两个工段。发电工段除设工长外,还有专门维修人员,兼管城内电网的维修。
1955年,发电厂投资6万元购置了阳泉某厂转让的上海通用机器厂生产的375马力蒸汽机带240千瓦发电组一套,于1956年6、7月安装发电,原128千瓦发电机组调往昔阳县。平遥县城一时供电充足,动员群众用电。又购置升压变压器升到3300伏后升至6600伏,架设线路5千余米,送往平遥火柴厂,当时该厂自备60千瓦发电机组供电,自此改以平遥发电厂供电为主。政府机关、平遥中学、医院,不少居民都用上了电。1957年开始向东城送电,这是农电的开始。1958年春夏,平遥发电厂又建设了两条6.6千伏高压线路通往岳壁、桥头,供其电灌站和居民用电。1959年1月2日,太原供电局筹建的平遥新庄35千伏变电站正式建成投运,从介休变电站110千伏电网上引出了35千伏供电,平遥改由太原大电网供电,平遥发电厂逐步退出了供电网。历时35年的早期电业完成了历史使命,平遥电业展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电业。
1.《2019民国煤油灯专题之煤油灯下的记忆》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2019民国煤油灯专题之煤油灯下的记忆》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521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