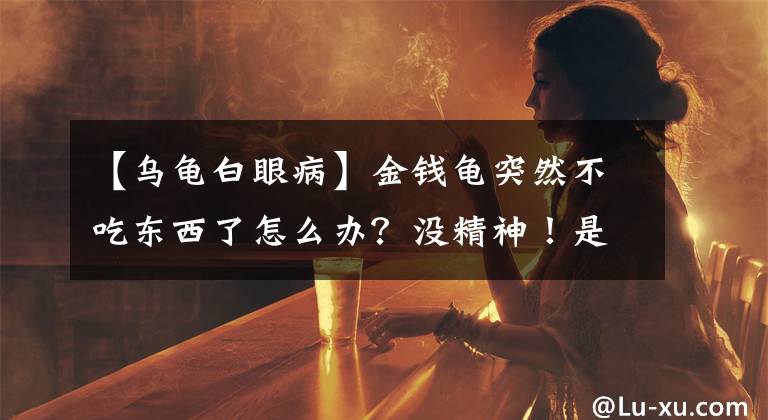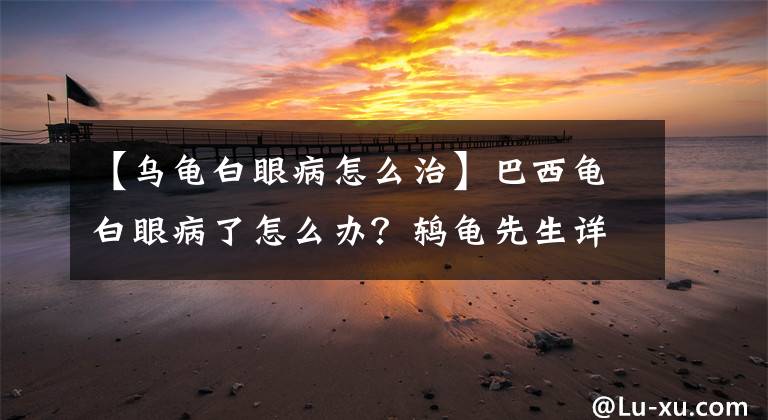人生最可怕的是失去希望。
农历2月,已经是草莺飞、春光明媚的好季节。
田里的草儿开始冒青,攒足了一个冬天的劲,顶着碎石子,开始往外长。河堤上的两排粗壮的柳树,远处一瞧,好像头上陇上一层浅黄,近看,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倒是迷惑了好多小孩子的眼。再等些日子,大约他们是要折些新鲜柳条,编个草帽儿戴在头上,或者是将柳树皮滑下,做成小喇叭吹着。大人们也不太管他们,随着他们性儿,若真闯出了什么祸,连打带骂批上一顿。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心性的,眼泪一干,又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哪里还记得刚刚的皮开肉绽呢。
我家前院二嫂子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最没记性,一天能挨上十八顿打。我们都笑他橡皮脸,他年纪小,不觉得羞,只要有好吃好玩的,才不管他什么脸呢。这个孩子有个特点,不管他在家吃没吃饭,吃得饱或吃得不饱,和他妈妈来到我们家总会缠着他妈叫唤,“我饿!我饿!”二嫂子是从不留情的,往往这时候总是扬起手来朝儿子屁股上狠狠拍去:“刚刚吃过饭,你饿啥子嘛?看老子不打死你这龟儿子。”她操着一口纯正的四川话训斥着在我看来也有些调皮的儿子。我们都笑她:“二嫂子,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为什么要自称老子呢?”
“我们那个都这么说。”她每次都这么反驳,我依然觉得奇怪。
我的这个二嫂子,怎么说呢,虽然按辈分我叫她一声嫂子,但她年龄倒是比我妈妈还要大上近十岁,她不是我们本地人,是从四川过来的。这个不算奇怪,村里头好多像她这样的女人。有从云南来的,有从贵州来的,有从陕西来的。但那些女人因为都是不到二十岁就到了这个地方,说的话几乎和我们很像了,只有二嫂子,过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在这生活近了十年,但还是说着地道的四川方言。
二嫂子的丈夫是个半瞎子,一个眼睛完全陷进去了,听说是小时候害了眼病眼睛就没了。因为眼睛或是因为贫穷谁知道呢?反正一直都没有讨到老婆。等到年纪大些,陆续有些妇女被中间人介绍到他这里。这些女人有些是被骗子骗过来,有些自己就是骗子,但都没有待上多久就或跑或逃了,二哥依然是一个人。
听说他认识这些女人后都会带她们到县城的澡堂洗一次澡,二嫂子来的时候也不例外。邻里乡亲都说这去了澡堂估计又是待不久,这是邪性。但二嫂子确实不一样,她压住了这个邪性,不知道她是不是被骗子骗来的,但我却知道她实是想逃离她原来的生活了。她原来的丈夫很是槽糕,糟糕到她撇下了十岁的女儿跨过了大半个中国去逃离,她想破茧重生了。
她来到没有多久就怀孕生了个男孩子。她身体很是强壮,家里户外都操劳着。她那么努力想让生活好起来,大约她想让她不符“伦理”的逃离变得有意义。
二十几年前的农村还是那样的贫瘠,但是大家都是那样努力着。努力攒钱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将土坯房换成三间敞亮的大平房,或是攒着上学钱,期待自己的儿女能够上大学,拿个“铁饭碗”,不再受同样一份罪。
二嫂子也是这样努力的。
以前的冬天是农村里最安逸休闲的日子,也没有现在各种厂子招工。妇女们常常聚在一起聊起家长里短,为丈夫孩子打着毛衣。二嫂子是最心灵手巧,什么样的花色她瞧一瞧都能够织出来。邻里头的妇女都常常求助她来打毛衣,她也是热情的,只要有空都是揽下来。我妈常说,你这二嫂子这般聪明,要是小时候能上学倒真能上出个名堂来。
她的丈夫二哥也是个热情的人。他大哥追随媳妇去了云南讨生活留下一双儿女交给了他照应。他三弟媳妇跑了,自己也去了外地给人修车,留下一个男孩子也给了二哥照应。这是小的,老的还有年迈的父母,二哥不含糊,都应承着。
那时候放学后我家里头要是没人我会跑到二嫂子那找她玩会,她要不就是做晚饭,要不就是做猪食。那会子她也年近五十岁了,但还那么有干劲,她告诉我二哥和她说过过几年攒些钱就将房子换成平房。她说的时候眉眼笑着的,大概那是她那几年的希望吧。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二哥的侄子侄女和二嫂子吵架。她们对自己婶子说的话很不敬重,我听着都不大舒服。不过吵归吵,回头二嫂子却还是待这些孩子如初。最让人气不过的是二嫂子的婆婆,她身体不好,全是二嫂子前后伺候,但她却常常责骂儿媳妇不尽心。二嫂子有时候不放心上,照样细致伺候。有时候却自己偷偷抹眼泪,只是二哥却从没有言语上给些安慰。
二嫂子和我家走得近,妈妈倒是常常开导她。但是她慢慢地越来越泄气了般,有时候也不言语什么。后来她越来越多说起她原来的家,说她对不起自己的女儿,在女儿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说她原先的丈夫常常打她,说那个家太贫穷了,还说她家族的人都活不过50岁,家里的哥哥姐姐都不过五十去世了……妈妈常说她不要信那玩意儿,不过巧合罢了,可是这世界确实有太多巧合了,太多了就得叫宿命了。
背地里妈妈倒是常和我说,也怪不得,你二哥不尊重她,丈夫家里头人自然也不尊重了。那时候我还太小,并不懂得这其中道理。
二零零五是不一样的一年。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生死别离,我的爷爷没了。看到爸爸在灵前哭泣的时候我突然间又害怕又心痛。那是我第一个见爸爸哭,我有点不知所措。妈妈常常唠叨爷爷的不好,却也忍不在爷爷下葬时流泪了,你看人和人只要有羁绊了就会有感情,这种羁绊不一定非的是美好的。爷爷丧礼后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恍惚,我不知道人死亡后到底是灰飞烟灭了还是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存于世间。但那种真切知道一个人你生命中消失的无可无奈却常常侵蚀着自己,生命存在与消失带来的是一种无解的惊愕。
这种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在那年没有停止。农历五月份的一天我放学刚到家,妈妈看见我有些焦躁,和我说:“你二嫂子喝农药了”。我震惊极了,怎么会呢,她还等着盖平房呢。 “她是决心要死了,在药里添了油,这是断了后路救不回来了”。妈妈言中了,天还没黑的时候二嫂子被从医院接回来了,法医过来鉴定后家人就准备葬礼了。
那天天气很是燥热,大晚上的蝉鸣依旧不断。妈妈去看了二嫂子最后一眼,回来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她有些气愤像是打抱不平:“是你二哥把她所有希望给断了……”
那时候正是栽水稻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田里忙着。大哥三哥虽人到了外地,但却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田地。或许因为车票太贵或是什么他们在这个农忙没回老家,把地都托了老二照应着。二哥自己的水田不管,和二嫂子两个人一起把大哥的水稻种完了,又把三弟的收拾好了。剩下自己的大概实在是太累了,二哥说我们花钱让人干吧。这句话轻飘飘的像一根稻草,但却足以压倒那时候的二嫂了。那时候大家都太穷了,那时候二嫂子正憧憬着盖新房,二哥却还说大哥的孩子大了若上不成学,很快就要房子娶媳妇了,先帮着大哥把房子盖起来。这个女人在这些年里慢慢磨损的希望彻底在这个农忙里破灭了,她跨过大半个中国也没有破茧重生。
她终于还是没有逃脱她家族的诅咒,那年她正好五十岁,撇下了刚好也是十岁的儿子。
二哥很后悔,那会常常喝到大醉跑到我家和爸妈唠叨。一会说他错了,不该不顾自己的家,不看重自己的老婆;一会说二嫂子托梦告诉他,她要回四川老家归根了……絮絮叨叨,他那时候想起要珍惜自己的老婆来了。慢慢的他渐渐从失去妻子的悔恨或者伤痛中出来,开始努力赚钱。前些年盖了新房,给儿子娶了媳妇。他大哥把一双儿女带去了云南没有再回来过,三弟也又娶了媳妇开始了新生活。或许二嫂子再等等呢,日子或许就好起来了。
1.《【乌龟白眼病】扭转不了的宿命》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乌龟白眼病】扭转不了的宿命》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pet/24719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