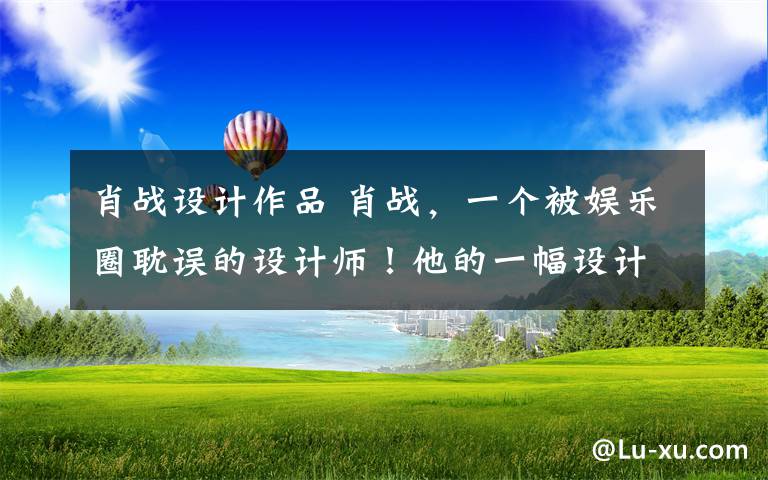《文慧阅读周刊》第1772期第一、第二版“特稿”
曾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的军事作家彭景峰,因长篇报告文学《解放西南》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短篇小说《驿道上的梨花》入选全国初中学生教材。他最后一部与文学有关的作品,沈从文的《谈艺术与绘画——1981年沈从文给我的一封信》,于2018年4月2日刊登在本报头版。7月24日是彭景峰逝世一周年。本刊特刊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馆长陈的《彭景峰印象不深》一文,以示怀念。
彭景峰不禁赞叹,陈
——熟悉文坛的老师去世了,我会尽力去找他们的书重读。我无法做任何深入的研究。我只是翻翻,珍惜一点点回忆,送点哀思。有时候看书的时候,突然对这个曾经熟悉的作家感到“陌生”。以前当然看过。如果再翻一遍,感觉真的对作家的文学成就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认识。同理,如果再细细品味死者的艺术特色和语言风格,会得到很多启示,甚至会觉得对他们创作个性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当然,也许是因为我经历过一些文学事件,看过逝者的回忆,以及他们当年的演讲,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真相”,也知道了各种观点,也是有趣的,有益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引起了自己对某些事件和某些人的重新评价,引起了自己对自己心理轨迹的反思,等等。我想,为了缅怀一位老师和朋友,“痛并愁”,人们共享一颗心。然而人都走了。想想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见思奇”应该是更长的记忆。

▲2015年彭景峰在其住所门前
他的文学抱负和童心依旧
我和彭景峰很熟,记得早些时候在穆峰同志家里见过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穆峰的家在登势西出口的黄土岗胡同。我去的不多,但几乎每次遇到文坛的作家和评论家。印象最深的是认识了几个云南的朋友。彭景峰在黄图邮政相遇。我记得是彭景峰先到的,当我看到另一个来自穆峰的客人时,我匆忙离开了。他走后,穆峰提醒我要把他和电影《边村篝火》、《芦笙情歌》联系起来。穆峰哀叹自己在1957年被“错误地划向了右翼”,而他重返文坛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年间,他因质疑林彪的“人格崇拜”而被囚禁七八年。穆峰说,难得的是他的文学抱负不变,他的童心不变。“你看过他重新进入文坛后写的《驿道上的梨花》吗?”我说我看过这部小说,刘的《班主任》应该是前后出版的。说这两篇文章不好,刘吴昕写得深刻,彭景峰写得漂亮...
——彭景峰去世后,我重读《陆毅梨花》,突然明白了穆峰所说的“童心不变”的含义。

▲《梨花》手稿
——哀牢山深处,两个又累又饿的旅人走进郁郁葱葱的梨花林,看到了空竹箅泥墙的窝棚。白色的木门板上,用黑木炭写着两个字。“请进!”一进门,虽然“壁炉里的灰是凉的”,但大竹床是“盖着厚厚的稻草”,“大竹筒里全是水”。又见“墙上写着几行粗粗的字:屋后有干柴,梁上竹筒里有米,盐辣椒”。由此,一个美丽的故事发生在陆毅路的梨花深处。以“我”一错再错,一遍又一遍地探查小屋主人,展现出一幅意境醉人、风情迷人的时代风光。试想,当时我们民族刚刚从“政治运动”的阴影中走出来,彭景峰刚刚回到他放弃的文坛。他献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这种美。岂不是“童心未泯”?
他更像一个坚强的长跑运动员
——想到彭景峰自报创作《驿道上的梨花》的缘起,不禁为这部作品有一点“概念化”而惋惜。但在突破僵化的文学思想束缚的同时,很难说哪些作品不带出痕迹。但这并不影响我在彭景峰重返文坛后“童心不变”的感觉。几年后,彭景峰的中篇小说《送你一朵白云》被《小说选》转载。他在文末的创作谈中写道:“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们伤痕累累的内心需要美和爱来安慰和欢呼。”他坚守的正是这种审美追求。然后彭景峰说:“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有垃圾,有闪光的东西...我也很讨厌垃圾,想参与打扫卫生,但是我感觉打扫完了,别忘了带人去打扫卫生的境界。”理解彭景峰的是他的朋友李国文。他说:“作家还是不拘一格的好。多加几套拳脚,多一些方式,可能更有利于表达千变万化的人生。”
——支持和实践文学的“思想解放”,但不要把“文学”局限于对苦难的揭示和哀叹,而要期待自己的文学把自己的人生引向美好干净的境界。这应该是彭景峰与“新时期文学”并驾齐驱,在“回归”后坚定地坚持自我认同的审美的证明。也许,这也决定了彭景峰不可能成为新时期文学繁荣的“旺”之一——尽管他曾获得过许多国家级奖项。他更像是一个坚韧的长跑运动员,脚踏实地的写自己的作品,依靠自己永恒的“志不变”,坚持同样的审美。彭景峰的作品涉及多种体裁,包括长篇、中短篇小说、影视文学剧本、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文、文学随笔和文学批评。他笔下的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人情,性格各异。据我记忆所及,他写的少数民族有瑶族、苗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傣族。他在云南边疆的生活历历在目,成了彩云南方的代表作家。

▲2009年彭景峰(左)和陈在北京合影
——尤其是他的非虚构文学,如《秦基伟将军》、《滇缅铁路节》、《夕阳之战——滇西中国远征军》、《解放西南》等,也以丰富的史料积累、广阔的历史视野、生动的描写征服了读者。我还记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和报告文学奖评委会上,评委们一致称赞彭景峰在虚构文学向非虚构文学的“转型”中所取得的成就,称赞他为撰写《西南解放》而阅读非虚构文学名著,看望国共两党的老人及其部下,查阅历史文献和档案,探索云贵川战场。用了12年,增删了十几遍,他才有了这部大作。评委普遍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作家的个人经历,也展示了作家对历史战略优势地位的思考,值得获奖。该奖项颁给了彭景峰,他说:“80岁的彭景峰,用他多年的手稿完成了西南解放。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全景再现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壮丽画卷,将战争融入民族史、军事史、情感史进行书写,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极具价值。”

▲《解放西南》手稿
他的批判性写作特立独行
——重读彭景峰,最难判断的是他时不时的批评。
——在文坛上,“得罪”彭景峰的人似乎太多了。
——他活着的时候,我听到点点滴滴的东西。有人说他鄙视“新潮”作家,有人说他的矛头直指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人甚至称之为“攻击”。一开始我不在乎。直到最近,当我读到彭景峰的《谈文学》时,我吃了一惊,这是他的文学理论集。在《文学论丛》《文学批评》《读后感》三张专辑里,我多年来都集中在他对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乃至文艺台词的评论上。虽然有文章支持鼓励新人,但是批评的火力够猛。坦率地说,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对个别作家作品的评价。但是,人已经去世了,似乎没有必要再讨论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彭景峰的批判话语,在夸夸其谈、空、不真诚、大打出手的文学氛围中独树一帜,真的有点“宁明死了,却生于沉默”的性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理想和追求,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充满了无数的事实和糟粕。挑战传统,立志创新,总是需要几个勇者,但也需要几个“时不时尖叫”的人去发现那些“皇帝的新衣”,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回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彭景峰,就像一只乌鸦在“栾香季风”飞翔。比如他对“文字必须称之为新潮”、“文学必须追求先锋”的“论点”的挑战,一度被误解,甚至被认为是跳出来反对“创新”的“左派”。回顾过去,他说“创新”要避免“取东方之精华,取西方之精华”。不是被文学实践所证实,被很多作家所接受吗?

▲2017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赴昆明看望彭景峰
——彭景峰《乌鸦之声》证明说话者无罪,听者全戒。有人说“不”,没必要急着取缔。
——翻阅彭景峰的批评,可以发现他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批评从不“东张西望”。所谓“左顾右盼”,就是他不会介意被人说成“左”或“右”,也不会在意批评对象属于哪个“圈子”,或者谁是神圣的。他不仅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局限性,还喊出了诺贝尔文学奖——从大江健三郎到莫言;他不仅抗议以“题材”为借口封杀文学的所谓“捍卫者”,还敢对“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辩手大喊:“拿点作品来看看!”……
——无论谁跟他有过恩怨或误会,无论他喜欢或不同意哪个观点,彭景峰都忍不住印象深刻。
——这样的作家是值得热爱和留恋的。
微信编辑周益谦
1985年以来的文慧书评
或者
whdszb
我们拥有神圣的学术热情
1.《彭荆风 彭荆风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 陈建功》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彭荆风 彭荆风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 陈建功》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tiyu/6866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