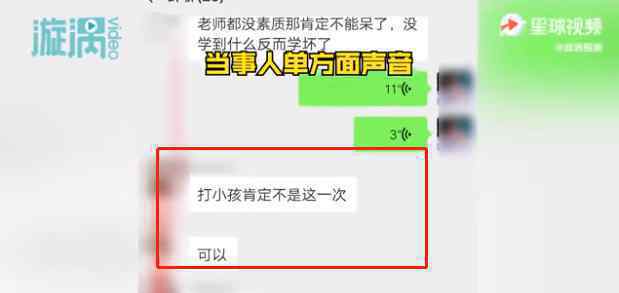罗中立神父
父亲和我
鲁德安
父亲和我
我们并肩走着
秋雨中休息一下
还有之前的雨
好像过了很多年
我们在雨中漫步
中场休息时
肩膀明显在一起
但是没有一句话可说
我们刚从房子里出来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长期同居造成的
滴水的声音就像折断的树枝
像冬天的梅花
父亲的头发全白了
但它几乎是一个灵魂
会让人忍不住尊敬
这仍然是一条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应该举手向他们打招呼
我和父亲都有说不出的善良。
安详地行走
挖掘
翻译:吴院长
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
拿着一支结实的笔,像枪一样依偎着。
窗户下,响起刺耳的声音
铲子正在深深地切入多岩石的土地;
我父亲在挖掘,我朝窗户下面看
直到他紧绷的臀部在育儿室
低弯,再直起。二十年来,
这种起伏的节奏贯穿了马铃薯垄
他以前在那里挖掘。
粗糙的靴子牢牢地踩在铲子上,长柄
用力撬膝盖内侧
他铲除了高茎,锋利的铲刃深深地插入土壤
我们拿起他撒的新土豆,
爱他们在他们手里又冷又硬。
对天发誓,这老头很会用铲子。
就像他父亲一样。
我爷爷一天挖出来的泥煤
比任何在托尼尔挖木炭的人都多。
有一次我给他送了一瓶牛奶
用纸不停地塞住瓶口。他挺直了身子
一口气喝完之后,他立刻弯下腰
继续切干净放草皮
为了得到更好的泥炭,把它扔到你的肩膀上
越挖越深。挖掘。
土豆地里、潮湿的泥炭沼泽中散发出寒冷的气味
铲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尖锐声音
穿透生命之根唤醒我的意识。
但是我没有铲子跟着他们这样的人。
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
手里拿着一支结实的钢笔。
我会用它来挖掘。

李自健神父
父亲
张躁
1962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还年轻,很理想,很左倾,但是穿着它
右翼帽子。他在新疆饿死了,
逃回长沙老家。他的祖母为他煮了一只锅
五花肉萝卜汤,里面飘着几颗红枣。
香在室内燃烧,香里有一种向上的迷茫。
这一天,他真的很无奈。
他想出去散步,但他不想。
他盯着看不见的东西,突然大笑起来。
他奶奶递给他一支烟,他第一次抽。
他说“奇怪的东西”几个字散落在烟圈里。
中午,他想去湘江边的橘子洲。
去练练笛子。
他走着,不想走,
他沿着路线往回走,突然觉得
总有两个自我,
一种是,
一个反过来,
一个人坐在一匹华丽的马上演奏歌曲。
而这个,走在五一路,走在不可磨灭的
现实中。
他想,不管是什么,现在都好了。
他停下了。他转过身来。他又朝橘子洲的方向走去。
他转过身,敲响了天空中的闹钟。
他转过身,打乱了世界上所有的节奏。
他转过身,一路上也很精彩
变成了我的父亲。
雨
翻译:陈东彪·陈子鸿
夜晚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因为此刻正下着毛毛雨
或者已经落后了。雨
这无疑是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到雨落下,谁就会想起它
那时,幸福的命运呈现在他面前
一种叫做玫瑰的花
还有它奇妙的鲜红色。
这遮住了窗玻璃上的毛毛雨
会在废弃的郊区
在一个不再存在的院子里
架子上的黑葡萄。湿帘颜色
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
我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

塞尚神父肖像
和父亲一起读书
雷平阳
太老了,不能迷路。
医生找不到旧的了
遍体鳞伤的灵魂,不得不在他
在畸形的身体上,寻找继续活着的人
概率:“面对一个没有别的办法
老年痴呆症患者,我们的
处方:找一张白纸,写下联系人
姓名、电话号码和家庭地址。"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做了,但我们仍然担心
如果这张纸在他的口袋里,
我也弄丢了。我们应该去哪里
寻找失去的父亲?他曾经
热衷于表达自己,来自新鲜
走着走着,骨头像一堆
装在皮囊里的碎钢条嘎嘎作响。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方法
皮下,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喜欢迷失,默默
回到家乡。我认为他的地方
一定有一架没有尽头的梯子
可以整天爬上爬下,就像轮回一样
每次我去看他,我都假装是个陌生人
不敢问他什么,怕他充满警惕
问:“你是谁?”
“我是你儿子!”每一个回答。
有一个生锈的钉子
果断钉,我的脊椎
昨天
翻译:董继平
朋友说我不是好儿子。
你明白吗?
我说是的,我明白
他说你知道
我不经常去看我的父母
我说是的,我知道
他说即使我住在同一个城市,
也许一个月后我会去那里
一次或更少
我答应了。
他说我最后一次去看父亲。
我说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
他说我最后一次见父亲的时候。
他问我打算做什么
我的生活和他
走进隔壁房间
给我带点东西
啊,我说
最后再感受一次
我父亲的手很冷
他说,我父亲呢
转过身来,看见我在大厅里
看我的手表,他
说你知道我想把你留在这里。
跟我说话。
是的,我说,
但如果你很忙,他说
我只是不想让你感受到你
你必须这么做
就因为我在这里
我什么也没说
他说我父亲
说也许
你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或者也许你应该见见
一个我不想留住你的人
我看着窗外
我的朋友比我大
他说,我跟我爸说是这样的。
于是我起身离开了他
如你所知
虽然我哪儿也不用去
你什么都不用做
“哎呀”
湿婆
我要飞去杀鱼
一刀下去
手指和鱼享受它,刀
同样的锐度
我“唉”了一声
父亲及时出现了
手里拿着创可贴
我被惊醒了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另一个世界,父亲
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手指了
他独自拿着创可贴
击打
“哎呀”我大声喊道

杜鹤·昌赣·罗中立
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美好的夜晚
翻译:吴宁坤
不要轻轻地走进那个美好的夜晚,
老年应该在日落时燃烧和咆哮;
愤怒,对光的消逝的愤怒。
虽然聪明人在临终前知道黑暗是合理的,
因为他们的话不会产生闪电,他们
我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美好的夜晚。
善良的人们,当最后一波浪潮过去时,喊出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在绿湾跳得很精彩,
愤怒,对光的消逝的愤怒。
愤怒的人们捕捉并歌唱飙升的太阳,
我知道,但是太晚了。它们让太阳在途中悲伤。
我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美好的夜晚。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耀眼的目光去看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发光和快乐,
愤怒,对光的消逝的愤怒。
你,我的父亲,在那悲伤的高处。
现在用你的眼泪诅咒我,祝福我。我求你了
不要轻轻地走进那个美好的夜晚。
愤怒,对光的消逝的愤怒。
成熟小麦
湖
那一年,兰州新出小麦
熟的
在水上生活了30多年的父亲
打后九穴
坐在羊皮筏子上
回家吧。
有人在搬运食物
晚上推门进去
油灯下
认出那是叔叔
老兄弟
沉默一夜
只有水烟壶
咕噜咕噜
谁的思想也是
半英尺厚的黄土
麦子熟了!
划,划,爸爸们!
——献给新时代的船夫
昌耀
自从我理解了海浪的节奏,
我们的触角,是如此的确凿
感受大海的戏弄:
-排,排,
父亲们!
我们出生在海里。
我们的胚胎史,
这只是我们的胚胎历史——
展示了从鱼虫到真人的进化顺序。
把脚蹼都脱了。
然而,我们仍在顽强地划船。
然而,我们仍在努力划船。
我们是一群男人。是一群女人。
它附属于一群女人
一群男人。
让我们摇一摇,划,划。
在天幕的金色黎明,
许多折回
庆功宴上有狂妄军队的醉态。
我们不会喝醉的。
最动情的呐喊
会不会是这样
我们沿着椭圆形的海平面前进
向前冲刺
嚎叫?
我们都哭着来到了这个多彩的世界。
后天的微笑是对母亲报纸的一瞥
舒适。
-我们又哭又笑
从海洋到内河,再到大陆...
从大陆到海洋,到拱顶...
我向长城致敬。
我在泉州湾看到了那艘古老的十二桅帆船。
我收到了春秋晚期的编钟。
我们会翻软文历史书。
从所有的器皿中,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
我听到流水之上的阻力的脚步。
-划船,父亲们,
划!
还有时间赶紧。
太阳不老,才中年。
我们会有自己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里程碑。
但是漩涡,
那凶猛的弧线,
永远不要放弃追踪我们,
只是扫一下
我们的父亲和兄弟永远在一起,
把幸存者的脊椎
扭曲了。
大海,我应该诅咒你的暴政。
但是摆脱压迫性的海洋不是
大海。迷失大海的船夫
也不
船夫。
所以,我们还是愉快地点着了火。
我们还是要激情切婴儿衣服。
我们用力划船...哈哈的笑...划船
...哈哈的笑...一行...
它跨越了冰河时代的洪水期。
是赤道风扫过火山灰。
穿过泥石流。通过
原始公社的遗迹
生物遗骸的沉淀物...
我们最初来自一个狂野的时代。
我们创造了大禹,
他是水边的神。
那个勇敢的女人
变成了一只回收的精卫鸟。
先知有很多。
总会有橄榄枝。
总会冲出必然王国。
但是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个体都是短暂的,
哈雷彗星难得见两次。
当古代之后的另一个未来
我们不再认识我们畸形的后代。
然而,我们仍在顽强地划船。
然而,我们仍在努力划船。
在这个不断缩小的星球上,
不会再有平坦的道路。
不会有别的选择了。
除了五件巨型袈裟,
我只看到渴望海岸的船夫。
只有海岸的呼喊
沿着椭圆的海平面
合并成一个分支
不松懈的
嚎叫。
大海,你永远不会被触碰。
我们的刀刃永远不会变钝。
我们婆婆冬天还需要腌制咸菜。
我们的女孩还需要烫发。
我们的胎儿还需要从荷花中取出
劳动。
.....今天晚上?
会有那么多孩子在分娩。
我不忍心闻孩子们的哭声。
但我们的刀片绝对忠诚。
这样划。这样划。
只需回答大海的调侃:
-划船,爸爸们!
父亲们!
父亲们!
我们不会喝醉的。
我们带着孩子们的哭声上路了。
在海的尽头
会有我们的
笑。
1.《写给父亲的诗 10首给父亲的诗,每一首都震撼心灵》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写给父亲的诗 10首给父亲的诗,每一首都震撼心灵》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10120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