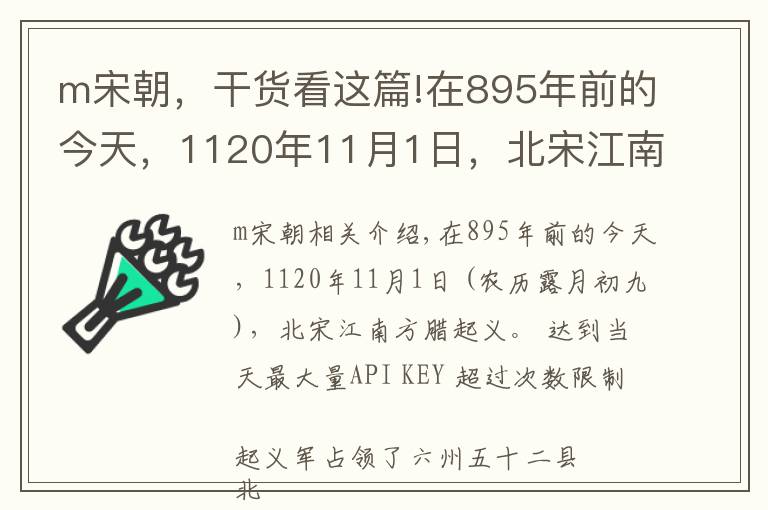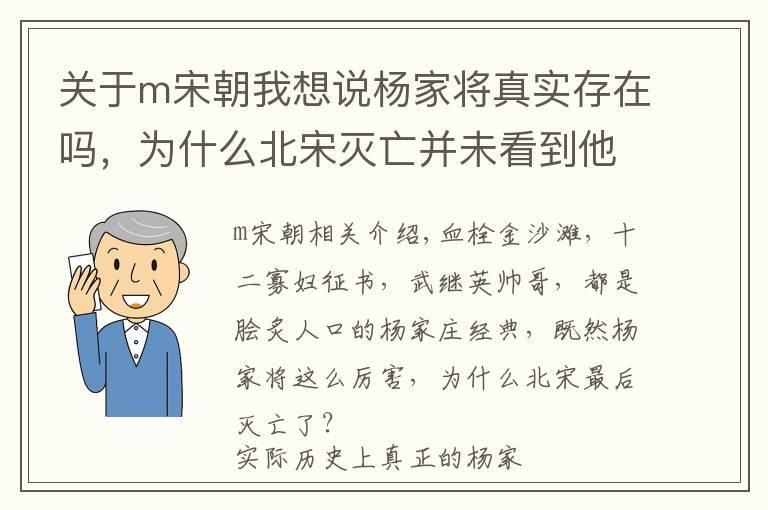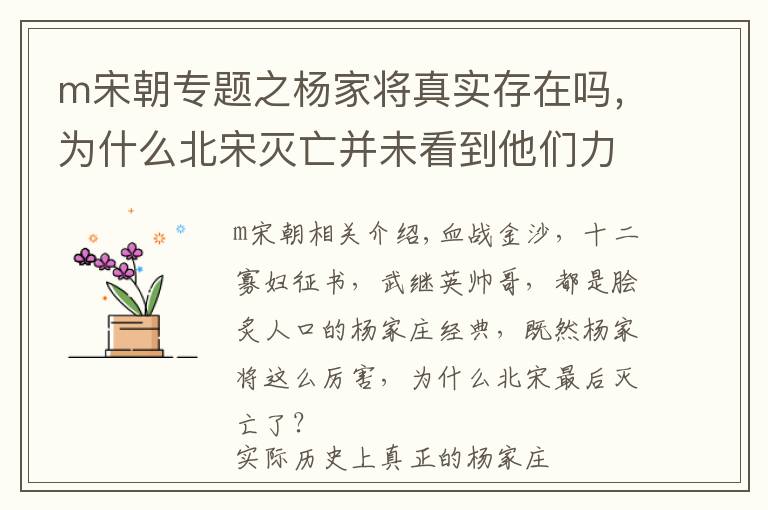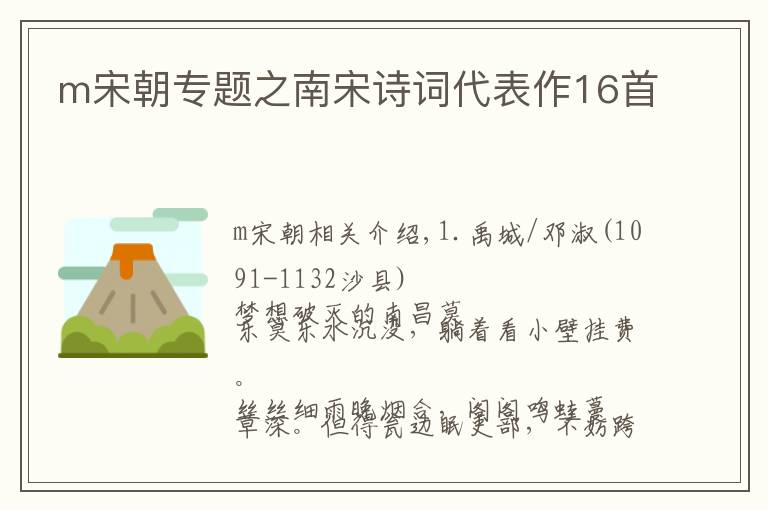宋元时期,长沙市从马楚国的都城下降到地方行政治理所,其规模和格局也随着军事、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长沙城到宋以后,在建制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将长沙县划出5个乡,湘潭划出两个乡置善化县。两县之界线,据黄朴华先生考证,系由大西门往东经石乐私巷出东长街(今蔡锷路)过大官园,至落星田,至浏阳门以北,小吴门以南。此线之南属善化,北属长沙。一城内两县分治,古城建制中较为少见,而长沙此种情况竟延续了800余年,直到民国建立后的公元1912年才合二为一。
北宋时期的长沙城,文献缺乏直接的记载,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癸丑(按:即1133年),赐潭州度僧牒二百,为修城之用。潭州自为敌所破,城壁皆坏。李纲以为汗漫难守,请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纲去。至是,安抚史折彦质言于朝。诏监司相度。其后诸司言:潭州城围二十二里九步,西临大江,东、南两壁并依山势,不可裁损,惟北壁地皆荒闲,欲截去城池七里半。新城围计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后亦不克成。”这段文字虽重点是讲南宋的情况,但其中提到的长沙城围“汗漫”,“潭州城围二十二里九步,西临大江,东、南两壁并依山势”,当是指北宋时长沙城的情况。“汗漫”即广大之意,“二十二里九步”约为12560米,说明长沙城的规模较大。但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万达广场、华远华中心工地上明清、南宋、五代三个时期的城墙是叠压关系,未发现北宋时期修造城墙的痕迹。长沙市文物考古所的黄朴华先生据此认为,北宋时期并未新建或大规模改造城墙,只是沿袭了五代时期长沙城的格局,但可能对城墙进行过一定程度的修缮。其四至范围,东在今芙蓉中路西侧一线,南在今城南路一线,西在今湘江中路一线,北线在今开福寺路北侧。宋代曾在城东定王台建长沙县学宫,并将长沙县治迁到此处。《湖广通志》引宋本《太平寰宇记》云:“定王庙在长沙县东北一里。”清代所编的《湖南通志》说,宋代在浏阳门内的长沙县学宫,至元代移至府学右侧。
南宋初年,因金兵破城以及刘忠、杜彦、孔彦舟、马友等几股溃兵、土匪武装攻打长沙,出现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说的“潭州自为敌所破,城壁皆坏”的局面。这样,加强城池的防御能力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时力主抗金的李纲上奏“请截三分之一”,以缩小防线,加强集中防御。李纲不久又被罢官,改造长沙城的事便被搁置起来。安抚史折彦质也有“截去城池七里半”的打算,“后亦不克成”。
至南宋末年,向士璧来镇守长沙,面对蒙古大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开始着手构筑城防,整修长沙城池,并最终完成了截城三分之一的工程,长沙城围定型为“十四里半有奇”的格局。
据上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对城墙的改造,主要是重新规划建造北城墙。因为,当时的长沙城“西临大江,东、南两壁并依山势,不可裁损,惟北壁地皆荒闲”,城围过大过长,不利于防守。因此截去北面“七里半”的城围,长沙城周长从“二十二里九步”缩小为“十四里有奇”。黄朴华研究后认为,将原长沙城北线(开福寺路)、西线(湘江中路)、东线(芙蓉路)三面城围的合计长度截去“七里半”(4200余米),则南移位置正好到达今湘春路一线。这一判断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据支持。湘春路一线的北侧保存有宋代护城河。民国初拆除长沙古城墙时,在湘春路发现古城门遗迹,并出土宋代石刻“云阳门”匾额,上面题款“景定庚申向士璧书并立”。景定庚申即1260年。证明北城墙及城门系南宋末年由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向士璧组织修建的,而长沙城池的全面改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自此,长沙城的格局基本定型。
据考古发掘,宋代城墙的西线与五代城墙西线的位置基本没有变化,只是稍有错位的现象,万达广场工地的宋代墙体与五代城墙西侧相邻,华远华中心工地的宋代墙体直接叠压在五代墙体的东侧之上,即是证明。根据芙蓉绿化广场工地发掘,宋元时期与唐代在同时使用东护城河,城南格局也未发现有变化的迹象,说明这一时期长沙东线和南线的城墙五代以来的沿袭。
至于城墙改造的方法,除局部利用了五代时期的墙体基础外,大部分系重新夯筑。这在潮宗街、坡子街等工地上可以看到,宋代夯土墙体内夹杂较多南宋时期的青瓷片和酱釉瓷片,墙体系新筑,且与五代时期的墙体略有错位。,因此,并非只是对原有城墙的修缮,更多的是重新筑造。而且,城墙两侧砌有多层青砖,加固城墙,加强防御。
黄朴华先生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南宋晚期至元朝时期,长沙城市的规模比唐五代更为扩大,其城垣四至范围基本为:东线自湘春路起,沿芙蓉路西侧→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到城南路一线,西到江滨(今湘江中路东侧),北到湘春路一线。平面呈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1400米的长方形格局。1该范围也与迄今考古发掘的同时期水井分布范围大体吻合。
这一时期主要的街市仍集中在西半城,特别是集中在德润门、驿步门、永丰街、万寿街、万福街、西长街、太平街、三泰街、坡子街一带老商贸区。这一区域之所以街市纵横,商贸活跃,人口集中,与靠近德润门、驿步门、潮宗门、通货门等水运码头不无关系,由于码头近,起运卸货方便,有利于商品货物的聚散。
汉唐以来,城市大都实行里坊制度,因其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自宋代开始,形成了按行业成街的开放式街巷制度,导致邸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大量沿街兴建,在苟安享乐的生活方式影响下,城市生活呈现多样化的景象。
宋、元长沙街市中的市坊,其繁盛的景象见诸历史资料的不多,仅有制墨业和刻板印刷业所形成的坊市因其在全国颇负盛名而略有记述。元代陆友《墨史》云:“长沙多墨工,惟胡氏景纯墨千金獭髓者最著。”“千金獭髓”是墨的品牌名,大抵为墨中精品。“州城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这些街巷的制墨业作坊,规模当不小,产品也极有名。长沙制墨业的兴盛与宋时刻板印刷业的繁荣是分不开的。北宋庆历年间,刘沆帅潭州时,以淳化官帖为底本,命僧希白摹刻于石,又增入伤寒十七日及王羲之、王蒙、颜真卿诸帖,置之郡斋。因内容丰富,摹刻精细,它们在社会各界影响广泛,因此摹本甚多,有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庐陵萧氏本等多种版本。因长沙在北宋时称潭州,故以长沙刘沆郡斋本印制的帖称为“潭帖”(又名“长沙帖”,以“潭帖”为祖本而支生的其他四家称“潭派法帖”)。潭帖在社会上能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因此长沙的刻板印刷工艺应和制墨业同样的发达,亦应有不少的作坊。
元代长沙城内还有一个昇平坊,坊内有著名的颜料生产工场。1985年,在我省沅陵县一座元代墓中出土了一张包颜料的包装纸,上有业主广告,说颜料为“潭州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长沙城街坊之内店铺鳞比,招牌临街高挂,其景象应是十分可观。
宋德祐元年(1275),元将阿里海牙围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固守三月后城破,当时元军已破湘潭并屠杀全城军民,由于阿里海牙的制止,长沙虽没有屠城,但守城将士及居民举家殉宋者不少,几乎十室九空,建筑亦破坏殆尽。元至和十四年(1277)复以土甓(砖)作城,并于他县徙民入城,城市才逐渐复苏。
1 黄朴华﹒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6:173﹒
1.《关于m宋朝我想说宋元时期长沙城的规模与格局》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关于m宋朝我想说宋元时期长沙城的规模与格局》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94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