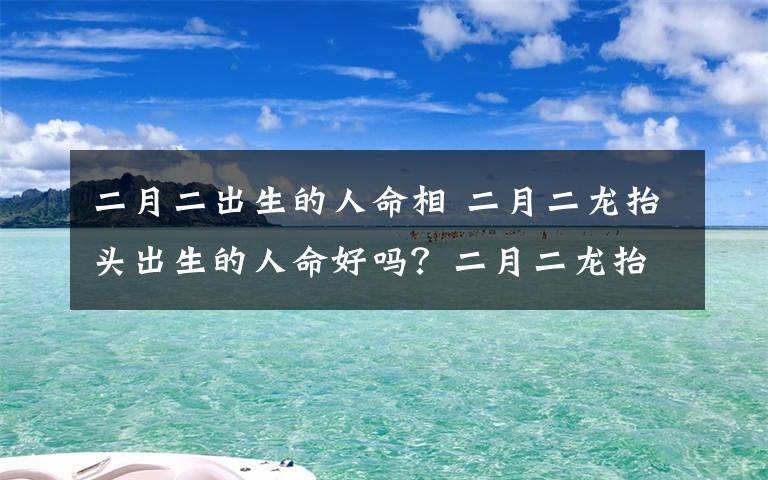"
第五十四章结束了,第九章也就结束了。你决定下一部小说读什么了吗?这些天记得给边肖留个口信。书单会在结束前整理好,给大家投票。还有,在这部小说之前,有人告诉边肖,他们想读* * *。边肖自豪地告诉你,小说的标题已经被我忘记了,所以请记得再发给我一次。错过了就要等到下次了。
54
尽管我泪流满面,脸上浮肿,王仍然冷冷地笑着,没有表现出任何宽恕。这个自鸣得意的女人,骨冷如冰,穿着我妈上官露诗为了方便我吃奶而创作的开窗衫。她用手指弹着金钥匙,看着我的表演。她确实有服装设计的天赋,这是必须承认的。我妈刚在我奶奶的大棉袄上挖了两个方便的洞,王却把那两个洞变成了表演的舞台。部分翻领卷有蕾丝的清式绿松石上衣,胸前有两个圆孔,孔的两侧与两个水红色“独角兽”的绣花文胸无缝连接空。这是桂林的风景,像强盗一样猖獗。是庄重的调侃,美丽性感。更重要的是,这件衣服打破了胸罩的私密性和季节性,成为引人注目的时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人上街,一定要考虑胸罩的颜色。要换衣服,必须换胸罩。胸罩一年到头都很畅销。对胸罩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现在我明白了,她做狐狸胸罩不仅仅是为了逗小红脸,而是为了做生意。美学对女性最美的部位,不分春夏秋冬,都给予了特别的呵护和强调。我知道她是无敌的。
“尹稚,一对夫妻一天可以享受一百天,”我真诚地说。“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问题是,”她笑着说,“我们甚至一天都没有一对夫妇。”
“那一次,”我回忆起1991年3月7日的夜晚,说,“那一次算不了什么。”
显然,她也在回忆1991年3月7日晚上的那一幕。她的脸赤红,仿佛刚刚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不是!”她气愤地说:“这只是无耻的猥亵,是不成功的强奸。”
她捂着脸,这是她1991年3月7日晚上的习惯动作。可能她在捂着脸偷偷用手指看我。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91年3月8日凌晨,红色的光晕映着窗帘。因为吸了一晚上奶,脸颊酸痛,麻木,肿。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阳光下,像一条怀孕的雌性泥鳅。油性,金色和黑色的斑点和图案。那两个流血的乳头,就像泥鳅的胸鳍一样,随着她的呼吸,有节奏地可怜兮兮地抖动着。我试着给她穿上天蓝色胸罩的时候,她闪了一下肩膀就扑到床上了。她躺在床上哭。高耸的肩胛骨,深深的脊沟。一个粗糙,有鳞的屁股。我试图用被子盖住她的身体。她玩了一把漂亮的,鲤鱼可以玩一把漂亮的,泥鳅也可以玩一把漂亮的,她带着泥鳅跳下了床。她捂着脸哭着冲到门口。她大声喊叫,声音那么大,吓了我一跳。可耻的人,可耻的人,你怎么能让我活着?如果一个赤裸的女人泪流满面地冲出上官金童的房间,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女人显然处于半疯半疯的状态。1991年3月8日凌晨,人民街上暴雨如注,毛毛虫般的杨树浸在里面,空调压着。国际妇女节是保护妇女的法定节日。我怎么能让她就这样跑出去了?如果让她跑出去了,不到十分钟,她就会口含鲜血僵硬地躺在路上。她绝对冒着生命危险。不清楚是车撞了她还是她撞了车。说清楚有什么意义?我似乎听到了汽车前部撞击她的可怕的油腻声。就像被澳洲车撞死的裸体袋鼠。袋鼠从不穿衣服。我不顾一切地冲到门口,弄断了她一只转身扭门把手的手。
她使劲挣扎,用头撞我的胸口,用牙齿咬我的手。放开我,我活够了,让我死吧,她大声叫道。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厌恶,对一个伪装成纯洁少女的女人的厌恶。更可怕的是,她用头撞门板,然后更用力,摔门板。我很害怕。如果她在门板上被杀,上官金童将会经历至少15年的劳动。再过十五年,我就不回来了。当然,我是被枪毙还是被囚禁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严重的是因为我,让一个女人胡来。你真是个混蛋!你为什么邀请她进来?后悔药没卖出去,但当务之急是安抚安抚这个想毁掉一切的单身女人。我抱住她的肩膀,悲伤地说:“姑娘,我会对你负责的!
她停止了挣扎,但还是哭了,说:“我生来就是你的人,死了就是你的鬼。”。我说:姑娘,我们俩都不幸福——到了天尽头,我们相遇了。我们理解。熟人有什么关系?,走吧,登记结婚。我不想要。我不想要你的同情。她脸上疯狂的表情消失了。我很惊讶地面对这张突然变得现实的脸。
她把91年3月7日定义为“无耻猥亵,强奸不成功”,这让我很吃惊,也让我很愤怒。这样一个翻脸不认人的女人有什么好怀念的?上官金童,你一辈子都有鼻子。你就不能努力奋斗一次吗?把这家店给她,把一切都给她,你就想自由。我说:“那么,我什么时候办理离婚手续呢?”
她拿出一张纸说:“你只要签个名就行了。当然,”她说,“我会尽全力给你3万元让你安定下来。拜托。”我签了。她给我开了一个上官金童账户的存折。
“不想让我出庭什么的?”我问。她笑了:“一切都是有人处理的。”她扔给我一张已经办妥的离婚证,说:“你自由了。”
我撞上了小脸红,对着对方谦逊地笑了笑,二话不说地说了声再见。戏终于结束了,我真的觉得重获自由很轻松。那天晚上,我回到妈妈身边。
在她母亲去世之前,大连市市长鲁胜利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死刑,缓期一年执行。耿连连和鹦鹉汉因受贿入狱。他们的“凤凰工程”其实是个大骗局。鲁胜利借给“东方之鸟中心”的上亿元人民币,有一半被耿连连用于行贿,其余被挥霍一空。据说光是“东方鸟中心”的贷款利息每年就要4000万元。其实这笔债永远也还不清,只是银行不希望“东方之鸟中心”破产,大蓝市也不愿意让“东方之鸟中心”破产。这个恶作剧的中心,鸟儿飞走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鸟儿流连忘返,鸟儿长满了羽毛。工人走自己的路,但它依然存在,存在于银行账户中,像滚雪球般的高利贷一样自欺欺人的利益滚动,注定没人敢让它破产,没企业能兼并它。
失踪多年的沙枣,不知从哪里回来了。她保养得很好,看起来像三十多岁。她来到塔边,看着母亲,母亲却反应冷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和司马亮有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恋情。她拿出一个玻璃球,说是司马亮送的承诺礼物。又拿出一面大镜子,说是她送给他的承诺礼物。她说她还是为了司马亮守贞。住在桂花大厦顶楼总统套房的司马亮,对自己的回归有很多担心,也没有心思去追沙枣。沙枣如跟随者般紧紧跟在他身后,恼得司马亮咧嘴一笑,跺着脚高高跳起,怒喝一声:“好表哥,你要什么?”你不想要钱,衣服和珠宝。你想要什么?!”司马亮甩开沙枣抓着他的手,愤怒地无奈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踢起一个细颈大玻璃瓶,水溅了一桌子,湿了地毯,十几朵紫色的玫瑰凌乱地挂在桌子边上。沙枣穿着薄如蝉翼的黑裙子,跪在司马亮身边,黑黑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司马亮的脸,不由得司马亮不看她。她的头很精致,脖子细长光滑,只有几条细小的皱纹。对女人很有经验的司马亮知道,脖子是女人藏不住的环。50岁女人的脖子如果不像臃肿的大肠,就像腐朽的枯木。沙枣五十多岁了还能有这么光滑挺拔的脖子,实属罕见。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维护的。司马亮低头一看,只见她两个凹陷的肩膀和裙子里朦胧的乳房。不管她往哪里看,都不像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一朵被冷藏了半个世纪的花。
是一瓶埋在石榴树下半个世纪的桂花酒。冷的花等着摘,浓的酒等着喝。司马亮伸出一根手指,戳了一下沙枣光溜溜的膝盖。她呻吟着,满脸是血,仿佛是晚霞。她像一个不怕生与死的英雄,扑到司马亮的怀里,抚摩着自己的胳膊,紧紧搂住司马亮的脖子,紧挨司马亮脸的滚烫的胸膛,揉啊揉啊,揉得司马亮鼻子里都是油,眼泪都流出来了。沙枣说:“马良兄弟,我等你已经三十年了。”司马亮道:“皂花,不要这样。等了我三十年,头上是什么罪。”沙枣说:“我是处女。”司马亮曰:“女贼为处女。如果你是处女,我就跳楼!沙枣委屈地哭着,嘴里嘟囔着,上蹿下跳,上蹿下跳,裙子像蜕皮的蛇一样掉在脚上,仰面躺在地毯上,喊着:“司马亮,你试试,我不是处女就跳楼!"
司马亮对老姑娘沙枣的尸体油腔滑调地说:“真奇怪,真奇怪。你是他妈的处女。”虽然我的嘴很苦,但是我的眼睛里有两滴眼泪。沙枣快乐地躺在地毯上,身体像个死人,但眼睛却湿漉漉地盯着司马亮。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陈年枕头的酸味,他看到沙枣花的身体瞬间布满了皱纹,一块块铜钱大小的老年斑也从她白皙的皮肤上铺开。就在司马亮大吃一惊的时候,强茂歌剧院的一个大肚子女演员推开门走了进来。
没有这个大肚子,她的身体真的很好,可以用苗条优雅来形容。现在她嘴直,嘴唇又黑又紫,脸颊上有几个蝴蝶斑,好像卡得很硬。
“你是谁?”司马亮冷冷地问道。
女演员哇的一声哭了。坐在地毯上哭,用双手拍着我的肚子:“你有责任,你让我怀孕了。”
司马亮打开笔记本,找到了与女演员有关的记录:晚上,招了强茂戏班女演员丁某陪她上床,做完后发现避孕套破了。他合上书骂了一句:“妈的,产品质量太差了,真要命!”
他拉着女演员的胳膊,从房间里跳了出来。女演员挣扎着说:“你带我去哪里?
我哪儿也不去。见谁都丢人!”他捏了捏女演员的下巴,阴沉地说,“做个好孩子,没什么可失去的!“女演员被陛下降服了。这时,他听到沙枣在默默地呼唤他:“马良兄弟,别走..."
司马亮招招手,一辆出租车像橘甲虫一样滑了过来。戴着红黄帽子的酒店门卫给他开门,他把女演员推了进去。
“去哪里,先生?”司机僵硬着脖子问道。
“消费者协会。”司马亮说。
“我不去,我不去,”女演员喊道。“为什么不呢?”司马亮用灼热的目光盯着女演员的眼睛说:“这是公平的事。”
出租车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兜圈子。道路两旁,工地还连着工地,有拆的,有建的。工商银行大楼已经被拆成两半,十几个灰头土脸秃顶的民工像橡皮人一样,机械而虚弱地挥舞着锤子,在墙上敲着砖。碎砖块飞过马路中间,导致汽车轮胎爆裂。在街道两侧的建筑工地的夹缝中,有豪华的餐厅,餐厅的窗户散发出浓烈的酒味,使得路边的树木东倒西歪。不时有一些赤红的头像从铝合金窗框里伸出来,喷出五颜六色的粥。每家餐厅的窗户下,都有一群长着皮毛、皮肤肮脏的癞皮狗,等着抢被喷到窗外的东西。交通拥挤,尘土飞扬,出租车司机焦急地按着喇叭。司马亮看着窗外的一幕笑了笑,没有理会身边哀嚎哭泣的女演员。车子进了市中心的大转盘附近,差点和一辆霸气得像坦克的大卡车相撞。卡车司机,一个戴着白手套的红脸女孩把头伸出窗外,粗鲁地骂了一句:“去你妈的!”出租车司机轻蔑地问:“可能吗?”司马亮摇摇车玻璃,色迷迷的盯着女司机,大声问:“姑娘,跟我玩?”女司机喉咙里打了几下呼噜,吐了一下嘴唇,准确地向司马亮脸上吐了一口痰。卡车的后备箱里盖着一张带树枝的绳网,几十只绿毛猴子在车厢里跳上跳下,又叫又叫。司马亮对猴子们喊道:“兄弟们,你们是哪里人?你要去哪里?”猴子沉默了,朝他眨眨眼,做了个鬼脸。出租车司机绷着脸说:“鸟中心没建成,猴子中心能建成吗?”“猴子中心是谁经营的?”司马亮问道。“谁能做到?”出租车司机一打方向盘,车就带着一个骑摩托车女孩的大腿飞了过去,吓得一只拉着大车的驴跑成了稀屎,坐在车轴上的老农骂他;在五月沉闷的阳光下,他戴着一顶黑色毛皮狗皮帽子。车里有两筐金杏子。
司马亮牵着女演员的手和脖子闯进了市消协。女演员拼命挣扎,却难以战胜司马亮的神力。“消费者协会”的人正在打扑克,三个女人,对付一个男人。那人光秃秃的头皮上盖着十几张白色的钞票。
“哥们,我们投诉!”司马亮喊道。
一个红唇少妇斜眼看着司马亮,问:“有什么好抱怨的?”
“避孕套!”司马亮说。
打牌的人愣住了,然后变得像猴子一样活跃。秃子忘了撕下头上的纸条,跳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严肃地说:“两位市民,我们的消费者协会致力于为消费者服务。请详细描述你的受害情况。”
司马亮道:“五个月前,我在桂花大厦的商品部买了一盒‘幸福’彩色避孕套。我只和这个女生合作了半个小时,避孕套就泄露了。因为避孕套质量差,她怀孕了,如果流产了,肯定会对她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不打掉,必然导致计划外生育。所以,我们要向安全套厂商索赔一百万。”
两个中年妇女问:“你说你工作多久了?”
司马亮道:“才半个小时。”
中年妇女吐着舌头说:“我的天,半个小时!”
司马亮道:“半个小时。我喜欢分秒必争地工作。你不信就问她。”
女演员害羞地低着头。司马亮捅了捅她说:“你别低着头,安静!
你是直接受害者。你说,你是不是只工作了半个小时?"
女演员生气地说:“半小时?你好久没下来了!”
几个女工作人员尴尬嫉妒地笑了。
秃头问:“你们两个是夫妻吗?”
司马亮大吃一惊,问道:“什么夫妻?情侣都这样吗?你简直就是个混蛋。”
秃顶被司马亮说得张口结舌。
中年妇女说:“先生,你有证据证明避孕套破裂导致你的女伴怀孕了吗?”
司马亮问:“这需要什么证据?”
中年妇女说:“当然,如果鞋子破了,肯定有鞋子破的证据;高压锅爆炸,必须有破锅作为证据;如果避孕套破了,肯定有避孕套破的证据。”
司马亮问女演员:“喂,你留着证据吗?”
女演员挣脱出来,捂住脸,跳出门外。她的长脚又轻又有力,看起来一点也不怀孕。司马亮看着她的背影,狡黠地笑了。
司马亮回到桂花楼总统套房后,看到一丝不挂的沙枣花坐在窗台上等他。她冷冷地问:“你承认我是处女吗?”
司马亮道:“表哥,把你遮天的诡计藏起来!我滚出了女人堆,你想骗我吗?其实如果我真的想娶你,我还会在乎你是不是处女吗?”
沙枣花发出尖锐的嚎叫声,吓得司马亮出冷汗。坐在窗台上的女人嚎叫时,五官错位,眼睛发出的蓝光像毒气一样冒烟。他本能地向前走了一步。沙枣身子往后一靠,红色的脚后跟在他面前闪了开去。
司马亮叹道:“看这个,小兄弟。我要跳楼了。这不像司马Ku的儿子。我不想跳楼,我也不像司马Ku的儿子。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司马亮打开一把不知道哪个女人留在房间里的遮阳伞,说:“小兄弟,如果我摔死了,你可以帮我收尸。如果我不摔死,我就永远不会死。”
他打开花伞说:“奶奶,电灯泡捣蒜,一锤子买卖!”然后他从窗户跳了出去,像一个有叶子的成熟的水果一样倒下了。
我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头晕目眩,惊恐地大叫:“司马亮——马良——”司马亮不理我,好不容易摔倒,花伞怒放。楼下闲人仰脸欣赏奇观。鸽哨满天飞,鸽粪落入张口。沙枣花委屈的身体像一只小死狗,铺在水泥地上。司马亮伏在楼下一棵法桐树的胖树冠上,伞上挂着大花一样的树枝。人们从树枝的裂缝中漏出,把它们砸在修剪得像斯大林胡子一样整齐的冬青树上。树木像绿色的泥浆一样飞溅。闲人乱叫,围拢过来。司马亮却没事人一样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拍打着屁股,向楼上招了招手。他的脸五颜六色,像我们童年教堂的彩色玻璃。“马粮......”我热泪盈眶地哭了。司马亮散开人群,走到门前,画了一辆杏色出租车,打开车门进去。看门人戴着紫色的军号,笨拙地追着他。黑烟从出租车的屁股后面喷了出来,灵巧地拐过街角,钻进了街上的车流。它在街道两旁一排排暴发户式、破屋式、小家子气的楼房矫情下,在狗仗人势、摆姿势的丑陋状态下,突然消失了。
我抬起头,松了一口气,就像从一个大梦中醒来一样。阳光灿烂,照耀着大澜市那些醉醺醺的、懒散的、满怀希望的、充满陷阱的人们。在城市的边缘,母亲的七层宝塔闪着金光。
母亲虚弱地说,“孩子,和你妈妈一起去教堂,这是最后一次,”
我花了五个小时拐弯抹角,在强茂歌剧院演员宿舍后面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修复后的教堂,它被化学染料厂排放的污水浸泡成了紫色。
教堂坐落在几个老旧的平房里,并不高大庄严,却简单朴素。教堂前和小巷两边,都有包着彩色塑料布的自行车。一个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的胖胖老妇人友好地点了点头,让我们进去了。
院子里挤满了人,房间里的人更多。一个老牧师,说话含糊不清。一缕阳光斜照在高台上。在阳光下,他那双干燥的手就像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标本。观众中有老人和小孩,有一半以上是年轻女性。他们都坐在小长椅上,展开的圣经平放在膝盖上,手里拿着笔,书上有记号。一个和她妈妈很熟的女长辈找了两张小凳子,安排我们靠墙坐下。在我们的头上是一棵老槐树的巨大树冠,槐花盛开,像薛瑞一样丛生。香味令人窒息。粗糙的槐树茎上有一个磨损的角,扩大了传教士的声音。号角发出嘶嘶声,无论是老牧师的呼吸还是号角的呼吸。我们静静地坐着听讲座。
老牧师声音嘶哑地说,虽然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猜想他的嘴上一定挂着两个白色的泡泡。
“人,你应该善待他人,即使他是你的敌人。就像上帝教导的那样,‘如果你遇到了敌人的牛或驴并且迷路了,一定要把它带回来给他。如果你看到一个讨厌你的人的驴子躺在重物下,不要走开。一定要和驴主一起抬重物。" "
“人,不要贪吃,就像主教你的,不要吃‘雕、狗头雕、红头雕、鹰、幼鹰及其类;乌鸦及其种类;鸵鸟、夜鹰、鱼鹰、鹰及其同类;鸬鹚、猫头鹰、角鸮、鹈鹕、秃鹰、鹳、白鹭等;“戴胜的鸟和蝙蝠,”那些违反戒律的人受到了惩罚。
“人们,要有耐心,就像上帝教你的那样,‘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伸出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委屈,都不要抱怨。如果你受了罪,那是你应得的。即使肚子饿了,身体有病,也不要抱怨。今生的苦,来世的福。
你要咬着牙才能活下去。耶稣不喜欢自杀的人,他们的灵魂无法救赎。
“人,不要贪图钱,钱是老虎,养老虎的会被老虎伤害。”
“人,不要贪恋女人。女人是刮骨的钢刀,贪心的人用钢刀刮骨头。”
“人们,你们应该害怕,别忘了那天的洪水、大火。永远要想到主荣耀的名。艾曼纽,阿门!”
阿门!当听经书的人齐声呼喊时,许多妇女的眼睛湿润了。
在演讲台的一侧,有一种无声的钢琴声。唱诗班领唱,听经的人唱赞美诗。会唱歌的大声唱,不会唱歌的哼:“审判的大日子来了,那一天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一天会来。到时候圣人和罪人就要分左右两派了。你为这一天做好准备了吗?你为大审判日做好准备了吗?不管有没有准备,审判日都会到来。阿门!”
讲座结束了。基督徒拿起圣经,有的站起来打哈欠伸懒腰,有的坐在那里嘟囔。一个大裂口满脸痘痘的年轻人,嘴里叼着烟,一只脚踩在小凳子上,弯下腰,用10元人民币擦皮鞋上的灰尘。一个乞丐似的老人怔怔地盯着年轻人的手。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把圣经放进一个用丝线编织的精致袋子里,同时看着一只像白莲藕一样绑在胳膊上的小金表。她留着长发和披肩,红唇,手指上戴着闪亮的钻戒。一个肩宽面简的士兵把面值100元的人民币折叠成一条长条形,塞进一个绿色的捐款箱。墙上用粉笔写着四个字:伊玛娜利。一个哭丧着脸的老太太,坐在墙脚半块砖上,卸下身上的蓝布,拿出一叠卫生纸一样的煎饼,啃了起来。从强茂歌剧团的练功房里传来女演员吊着嗓子的声音:咦——啊——六月的一个大热天——第二个骑着毛驴奔向阳关的姑娘——咦——啊——啊。一个赤裸的男孩用尿滋养了一个蚁巢,汤倒进了蚁巢,蚂蚁们麻烦大了。一名中年妇女训斥小男孩,并威胁要割掉他的阴茎。小男孩不知不觉地抬头看着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弯腰拖着两条僵硬的腿,向一个正在给婴儿喂奶的女人走来。这个女人额头上有一块脏膏药,头发上有一些闪亮的血。一个腿上有疮的老人正光着腿坐在一个破麻袋上,一群绿头苍蝇附着在他流血的腿上。一只啄木鸟蹲在他凸出的膝盖上,飞快地啄着他的疮,从里面取出一些白色的昆虫。他眯着眼,望着太阳,嘴唇颤抖着,仿佛在念一个神秘的咒语。教堂后面的街道上,大喇叭里传来一声大吼:想发财,就少生孩子,多种树。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生二胎要结扎,提倡女结扎。
谁敢不结扎,罚款5800元。计生宣传车得意洋洋地开过去。酒厂的秧歌队来了。锣鼓喧天。八十个穿着黄色衣服、戴着黄色头巾的年轻人,和八十个穿着红色丝绸衬衫的大姑娘,一起扭动着,扬起滚滚尘土,穿过教堂的屋脊。这支秧歌队几年走遍了大澜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衣服浸泡在酒里。都是嘴里喷着酒气,扭着醉醺醺的秧歌,看似歪歪扭扭,实则法度严明。他们打着醉醺醺的鼓,男鼓手假装是古代令人生畏的英雄。教堂院子里的一些人被街上的锣鼓声所吸引,抬头望着屋顶外的红尘;有的低头,有的冷静,有的呆滞。屋脊上红色锈迹斑斑的铁十字架出现在尘埃里,就像耶稣的神秘面孔。一位戴孝的中年妇女哭着走进院子,她的眼睛肿成了水泡,只剩下两条黑色的缝。她发出悦耳的叫声,很像一首荒凉的日本歌谣。她手里拖着一根绿柳条,肥袍上沾满了鼻涕、口水和污垢。一只纤弱的瘦狗怯生生地跟着她,紧紧地缩着尾巴。她跪在头上戴着皇冠的耶稣画像前,大声喊道:“主啊,我的母亲死了,请保佑她上天堂,不要让她下地狱……”耶稣同情地看着她。从他额头渗出的血像珍珠一样滚了下来。三个穿制服的警察绕着门往院子里看,好像他们有所顾忌。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害羞地进了医院。那个用人民币擦鞋的年轻人跳起来,灰色的脸上挂着一层亮晶晶的汗珠。他似乎想逃跑,但三名警察已经进入一个部门,挡住了他的出路。他转身向教堂的砖墙冲去。他的身体在墙前跳了起来,双手抓住了长着细草的墙,脚趾在光滑的墙上踢了一脚。警察像老鹰一样跳起来,抓住男孩的腿,把他拉下来,压在地上。闪亮的手铐锁住了他的手腕。警察把他拖了上来,带了出去。他的半边脸沾满了灰尘,血正从他的牙齿中渗出。一个拿着保温箱的小男孩溜进院子里,用温柔的声音喊道:“冰棍!冰棍!奶油冰棍!”这个小男孩有一个大大的圆头,两只朗朗上口的耳朵,额头上有皱纹,黑色的大眼睛里有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绝望的光。他像兔子一样露出两颗长长的白色门牙。沉重的保育箱让他细长的脖子显得更长。他穿着一件破背心,肋骨突出。他穿了一条大裤子,使他的腿看起来像麻杆一样细。他的小腿上有些生脓的疮。他穿着一双号码很大的旧胶鞋,噗噗地走了。没人买他的冰棍,小男孩失望的走了。看着男孩痛苦的背影,心如刀割,可惜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教堂外的小巷里响起了男孩响亮的哭声。他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悲伤...
母亲坐在小凳子上,双手抱着膝盖。她闭上眼睛,似乎睡着了。没有一丝风,槐树突然垂直倒下。好像那些花瓣本来是用电磁铁吸附在树枝上的,现在被剪掉了。充满了兴奋和芬芳。天气晴朗。落在我妈的头发上,脖子上,耳轮上,也落在她手上,肩膀上。阿门!
这时,刚刚讲课的老牧师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教堂。他手里拿着门框,迷茫地看着槐花的奇观。他有着砖红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红色的大鼻子,浓密的黄色胡子,嘴里有着像耙子一样的铁牙齿。我惊恐地站了起来,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父亲。
李奶奶动了动脚,跑过来给我们俩介绍:“这是马牧师,马牧师的大儿子,从兰州回来主持教务的。这是上官金童,我们老成员上官鲁士的儿子……”
其实李奶奶的介绍是多余的,因为在她给我们起名字之前,上帝就开导了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知道了彼此的来历。这个混蛋,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在马洛亚的一个牧师和一个回族妇女的家庭,他用他那红大的、头发浓密的手紧紧地抓着我,蓝色的眼睛里噙着泪水。他说:“哥哥,我一直在等你!”
1.《丰乳肥臀莫言 莫言《丰乳肥臀》》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丰乳肥臀莫言 莫言《丰乳肥臀》》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shehui/778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