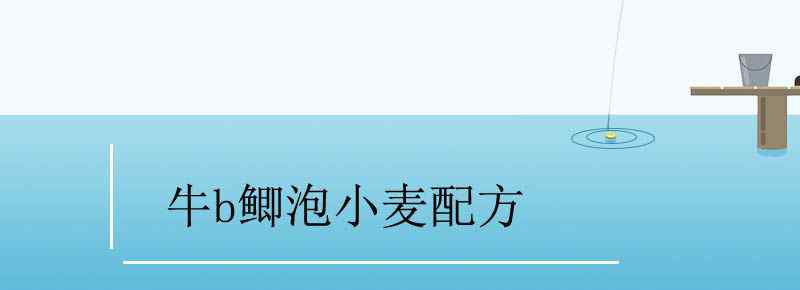小麦。小麦从麦秆上溅出并剥落。五月炎热的石板与一粒小麦相撞。
爸爸在太阳坝拼了两条高板凳,板凳用石板绑着。爸爸手里拿着稻草的一端,胳膊在空里甩出一个大圈。“啪——”麦穗重重地砸在石板上。麦秆就像一个正在艰难分娩的母亲,每一声痛苦的哭喊都在扼杀她的生命。麦秆的叫声,新生小麦的香味,爸爸泼的汗水,五月在村里打滚。
大战五月,“白毛儿”两兄弟带着弟弟和“白毛儿”来我家结麦子。“白猫儿”的弟弟比我大一岁。他没考上初中。他只在河对岸萧的自力更生学校学习了半年。他在家里的学习成绩最高。
“白发”他们有的是力气。他们的实力没了,对付自己的麦田绰绰有余。
川味猪肉在锅里煮。除了无限量的本地酒,水箱里还泡了四瓶啤酒,被认为是凉的。上村,人均分六分。“白毛”一家几口都是不满意的窟窿——六分粮,其他的可以等到收新麦。刚过完年,白发家族的粮仓就见底了。“白发”的哥哥只能带着“白发”到处挣饭吃。

小麦晒干了。水泉哥的磨前,有排队磨面的人。麻雀在磨坊外的电线上唧唧喳喳,一次又一次地叫着,飞着,像厚颜无耻的乞丐。在磨坊里,小麦香从咆哮的机器口中流出,像雾一样扩散开来。墙上的裂缝,角落里的蜘蛛网,屋顶上挂着的灯泡都是白色的。当所有人都把脸颊变白的时候,水泉哥变成了白头翁——一个白胡子的大侠。
没人来磨面,水泉哥就做细面。机器压出长长的面条,纺出同样的线。切的恰到好处,还是老样子。水泉哥的面挂在磨外阳光充足的地方。他拐进磨房,我们就像鸟儿一样溜出去偷面。放进嘴里,咔嚓,咔嚓,清脆。我们只敢掐掉几个小块。捏多了就暴露了!我们不敢偷一捆捆的面条回家,因为我们怕爸爸的黄晶条子。“白发”和他哥哥也害怕。“白猫儿”和他弟弟看着面条,咽了咽口水。磨坊紧挨着“白发”的房子,李走了下来。面条丢了,那就“黄泥糊裤裆——不是屎是屎”。坝上人要面子!
或者说,可以说在空文件里,水哥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白猫儿”和弟弟几乎是面条的义务监护人。
麻雀比我们还不要脸,啄了一地的面条。水泉哥捡起地上的面条,吹了吹灰尘。还有一个小簸箕。我们带了新的小麦做面条,两斤小麦做一斤面条。水泉哥知道白猫儿家的小麦不能和面条混在一起。他把从地上捡起的面条交给了“白猫儿”妈妈。“白猫儿”妈妈谢过她,收下,擦擦眼睛。晚上,白发家的烟也有麦香。

面粉回家。我妈第一顿肯定是炸油。面粉拌匀,葱切碎,撒上半把胡椒粉,拌入两勺豆沙。鲜榨菜籽油蜷缩在火锅里。新油和面,壁炉是蜡烛,铁锅是新房,热油慢慢软化面团体。
油块确实修补了破裂的婚姻。
崔芳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她嫁给了有裁缝手艺的姚叶。姚从长老室出来。叶瑶的父亲去世得很早。崔芳同情姚叶的母亲、儿子、孤儿和母亲,无视父亲的反对。她咬紧牙关结婚了。后来,姚叶的母亲也去世了。毫无节制,姚叶的慵懒本性日益暴露。生活不能继续了。崔芳想要离婚。
一个家,说分手。我妈妈很着急,所以她离开崔芳去吃午饭,让我爸爸去做姚叶的工作。叶瑶也挨擦擦。鲜红的油块放在餐桌中央。叶瑶什么也没说,低下了头。那顿午饭,从太阳出来空到太阳落到河对面的黑柏林,油像小山一样堆在桶碗里...
几年后,崔芳和姚叶设法结婚了。离婚的崔芳出了村,先是在省城穿衣服,然后有了自己的裁缝店,然后有了自己的服装厂。我妈妈和我一起在省城附近的县城定居后,崔芳带着她自己做的羽绒服来看我妈妈。崔芳和我妈妈讲了一个老故事,还提到了他们离婚时餐桌上的油块。娘后来说:“夫妻俩吵架,劝与不劝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崔芳记住了这个情况。”

妈妈会的。不仅仅是煎炸油。我从姨妈家的玫瑰里摘的玫瑰,被我妈拌上白糖,做成玫瑰酱,包在面包里,油煎,花香扑鼻,仿佛把春延带到了冬天;将面条铺上花,加入洋葱和青椒,拌成稀糊状,放入锅中滚出来,就像春饼一样。八月包上酸菜,配上鸡蛋清蘑菇汤,能让人暂时忘记对肉的思念;面条拉进煮好的饭锅里,一顿早餐又干又稀。我和姐姐把粥刮得满脸疙瘩。痘痘长期忍受饥饿,让我们整个早上都精力充沛。
第一次在街上吃馒头,不得不承认我妈蒸馒头是外行。没有碱粉,妈妈只能用上次剩下的旧面——馒头代替。旧面条埋在面粉里,已经完全脱水了。取出,打碎,转移水,作为碱水使用。黑发老馒头略酸。街上的馒头白白胖胖的。老馒头和白馒头的区别,似乎就是我们这些被晒黑的人和没接触过毒的街头小孩的区别。
就是那个发现让我知道了小麦的偏见。橘生淮南,橘生淮北。偏见小麦给街镇纯白,给荒芜的村庄留下灰色和黑色。巨大的铁皮机前,有人在抢着买白馒头。老馒头被现代的碾压车轮碾压,低声喘着粗气。我和海子一样,在别人认为“美好而温暖”的麦香里,第一次被麦香灼伤。
村里的青壮年都被麦香烧了。当一粒小麦一顿饭都不能丰富“白猫儿”和他的兄弟们的小康梦想时,他们就不能空守护麦田。他们去了遥远的城市。无法界定他们是逃出了小麦还是小麦逃出了他们。
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村庄里很少出现小麦。麦田还是麦田,油菜籽已经统一种植。种油菜籽挺省力的。帆布打开摇晃,油菜籽掉进布里,老人就可以收割了;种小麦很辛苦,需要轰轰烈烈的劳动。老人似乎看穿了割麦、捆麦、运麦的骗局,在石头上砸下一粒麦子,收割一粒麦子,就像二万五千里长征。

几年前,村外遥远的“迈克”把小麦收割机开到村里。但是,村里的梯田不是马平川的关中,想要穿越江湖的小麦收割机是挥不出拳头的。小麦收割机退出,小麦也退出。
村里,麦田空空。新麦的香味不再从磨里飘出来,不再从面架上往下流,不再从某个家的蒸锅里蹦出来。速冻小笼包和小笼包早就是街上小超市随时可以买到的食物。
一家人离开庄子后,我那被油炸过,撒过花,拉过疙瘩的铁锅,深深的埋在了破碎的土墙里。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玻璃橱窗前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糕点,让人隐隐约约地怀疑小麦曾经散发出一种让我们做梦的甜味。我们的麦香和牧歌已经被时间的洪流吞没,子弹也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一次又一次,像诗人海子一样,只能“独坐,梦见五月麦田里的兄弟……”
恍惚中,村里的麦浪又涌上心头。安静的日子里,云很轻很清。麻雀在水泉大哥的磨坊外飞翔,麦田的清香婉转地飘荡在广阔的田野里,唱着麻雀的歌,唱着金色的夕阳。

1.《幽微 宋扬:麦香幽微(散文)》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幽微 宋扬:麦香幽微(散文)》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caijing/12333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