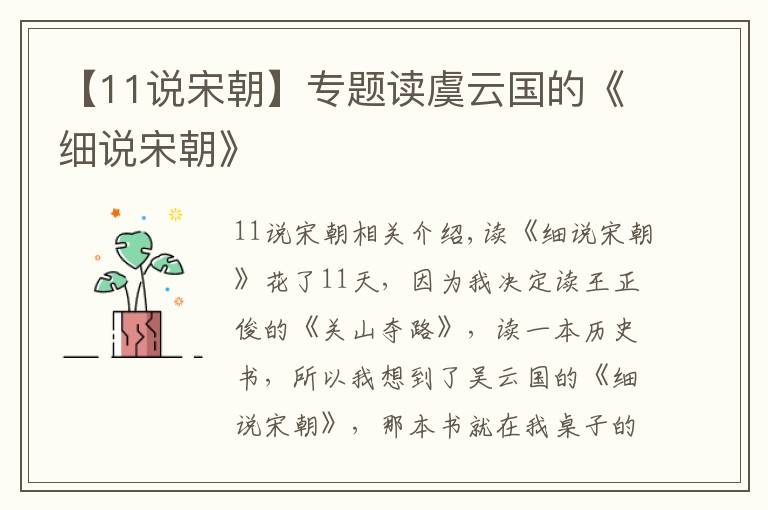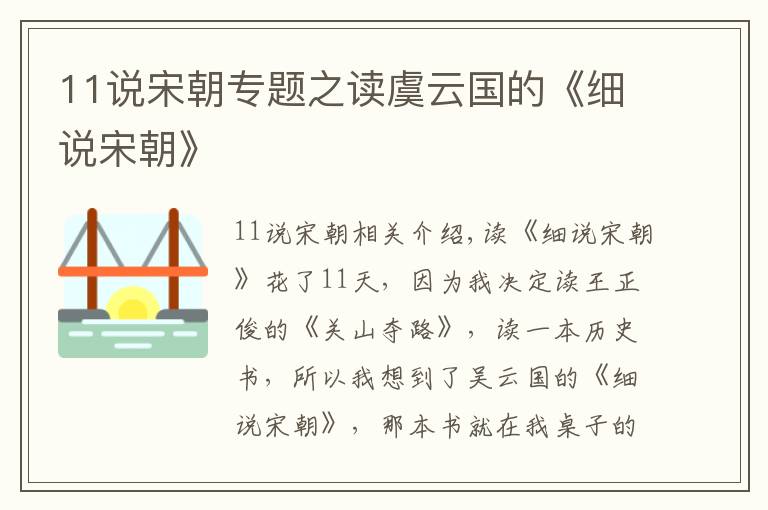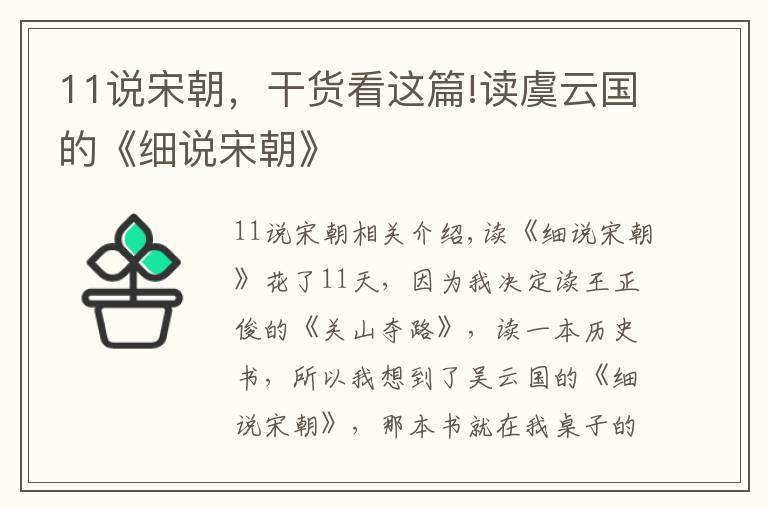黄波老师给了稿子,谢谢。
原文载有《宋史研究论丛》第27集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国庆节”的中世纪起源
卡里传统视角下的宋代“开放节”研究
文皇甫
黄波: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和藏族史研究,有《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等。
摘要:中国古代的“国庆节”的现象和观念,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开基节”,宋代以每年的正月四日为开基节,纪念和庆祝宋王朝的建立,这是汉、唐传统礼制中所没有的设计,也是对儒家经典礼学规范的突破。这是中古时代嘉礼举行的时间选择从自然时间的节气到人事时间的节日的转向。开基节虽然是宋徽宗时代的产物,但其产生,事实上可以追溯到真宗时代出现的天庆节,真宗君臣借助道教文化资源,突破了传统礼制的规范,打造出宋代庆典型节日的设置传统。但开基节的出现,却是宋徽宗时代对真宗模式的偏离的结果,这个纪念王朝开国功成之日的节日,恰恰是大宋王朝礼崩乐坏的象征。
关键词:宋代 国庆节 开基节
“国庆节”或“国庆日”(National day)对于一个现代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节日现象,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正式宣布“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1]国庆节的起源,基本上是近代中国对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吸收与再造,梁启超在清末发现,“中国向无所谓祝典也”,而外国则有许多“祝典”,“若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之七月十四日,为开国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2]对于“开国功成之日”的庆祝和纪念,即是现代国庆节最核心的内容。民国建立后,在确定国庆纪念时,也明确宣示“我国国节亦应效法法美,自是一定办法,即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3]
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国庆节,无论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思想观念,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交流互动中激发出来的,国庆节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种表现,[4]然而,中国古代是否真的不存在“国庆节”的现象和观念呢?中国历代王朝是否对自己政权的建立日的纪念和庆祝,拥有上述相关的行为或观念呢?关于中国古代国庆节的起源的探讨,目前学界似未有人注意,本文尝试以宋代的“开基节”生成与运行为线索,从中国古代的历史现象入手,以古代礼制演变为线索,探讨和解析中国古代的国庆节现象及其观念产生的历史进程。[5]
一、“古无是也”:宋代开基节对汉唐礼制的突破
宋代在每年的正月四日有一个官方的“庆节”,名为“开基节”。《宋史》“礼志”的“嘉礼”部分的“诸庆节”条下,有“正月四日有太祖神御之州府宫殿行香为开基节……皆如天节庆,著为令”的记载。[6]这一节日是徽宗后期设立的一系列庆节之一。开基节的日期为“正月四日”,这一天正好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日子。对于宋太祖称帝建国的情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述最为精详,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辛丑朔(初一日),“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癸卯(初三日),“大军出景爱门”,“是夕,次陈桥驿”,当晚开始谋划代周自立的事情,第二天,也就是甲辰(初四日)黎明,就上演了“黄袍加身”的情节,然后“整军自仁和门入”,晡时,“太祖诣崇元殿行禅代礼”,甲辰,也就是初四日,完成了周帝禅让和太祖即位的各种手续,赵匡胤正式成为“皇帝”。
但这时的赵匡胤其实还不是“大宋皇帝”。由于一天之内,从黎明的黄袍加身到回师京城,再到晡时以后的举行禅让和登基典礼,事情太多,在甲辰日这一天,宋朝君臣还没有来得及为新王朝确立一个新的国号,也没有来得及诏告天下新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这些事情是在第二天,也就是乙巳日(初五日)才完成的。《长编》记载,“乙巳,诏因所领节度州名,定有天下之号曰宋。改元,大赦”,并“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传赉诏谕天下。”[7]可以说,宋朝建立完整过程,其实是在正月初四和初五两天的时间里完成的。但从宋代官方确定的“开基节”在正月四日来看,宋朝官方是以太祖成为皇帝作为开国功成之日的标志,至于“大宋”国号的确立,其重要性当然不如皇帝身份的获得,《朝野类要》中揭示正月四日为开基节,也正是因为“周显德七年正月四日,太祖皇帝登位。”[8]王明清在所引徽宗时代的开基节建言的“进状”时则言“正月初四为创业之日”[9],其意都清楚地揭示出开基节的正月四日为宋代的“开国功成之日”的意义。
宋代的开基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类似于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庆节的历史现象,它不但由官方下令了确定了“开国功成之日”的具体时间,还对这个时间加以纪念和庆祝。然而这一行为和观念,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相当“另类”,可谓是汉、唐皆无之事。据《汉书》的《高帝纪下》,汉五年(前202年)冬十二月,刘邦在垓下之战中击败项羽,“楚地悉定”。当年正月(此时历法沿用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向汉王刘邦“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刘邦在表示谦让后接受,“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最后在二月甲午(初三日)[10],“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11]虽然刘邦即皇帝位的这一天,是功臣与儒生们一起精挑细选出来的良辰吉日。但是二月甲午(二月三日)这一天,在以后的汉代历史中却并不“特别”,史籍上见不到汉朝有对二月三日进行纪念和庆祝的行为或说法。
事实上,汉代礼制建设一直不理想,正所谓“汉兴,拨乱反正,日不睱给”,刘邦时虽然有著名的叔孙通制礼之事,但“未尽备而通终”,文帝时贾谊提出“兴礼乐”的设想,但遭到军功贵族反对,“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而汉武帝时代,“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睱留意礼文之事”。到宣帝时,王吉上书“愿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但“上不纳其言”。[12]因而终西汉一代,礼制不备就是一个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社会,当然不会对开国功成之日之类的如此细致入微的内容在礼制方面有所设想了。至于唐代,情况与汉代差不多,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戊午(十四日)[13],隋恭帝下诏逊位,遣使“奉皇帝玺绶于高祖”,李渊在辞让一翻之后接受,“隋帝逊于旧邸”,隋恭帝完成了退位的仪式,但是过了六天,到五月甲子(二十日)才举行了登基大典,“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李渊正式成为大唐皇帝。[14]然而与汉朝一样,五月二十日在大唐以后的岁月里,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见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宋代的开基节被放置到五礼的嘉礼之中,这一点在前揭《宋史》的编排中已有清晰的定位。但在汉唐王朝的以经典礼制为基础的规范礼制系统中,在相关的礼制行为和礼学观念的层面上,都没有纪念与庆祝开国功成之日的位置,正如《宋史》的“礼志”所言,包括开基节在内的宋代“诸庆节,古无是也。”[15]《宋史》所谓“正月四日有太祖神御之州府宫殿行香为开基节”,本质上是要选择一个日子来定期举行系列的常设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这跟近代以来的国庆节非常相似。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每年10月10日的国庆节,官方通常会举行阅兵、授勋、宴饮等活动;而民间则会举行集会、演说、提灯游行等活动。[16]
与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庆节一样,开基节也有着一些独特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如在“有太祖神御之州府宫殿行香”,即在供奉宋太祖画像的地方举行烧香仪式,这大概是开基节的专属纪念活动,《宋会要》对此有更详细的说法,“在京合于景灵宫皇武殿、州军于有太祖皇帝神御处烧香。” [17]此外还有一些宋代官方节日所共有的活动,即《宋史》所说“如天节庆”的系列令式,魏仙华对天庆节等节日的活动内容作过初步的梳理,包括官员休假、禁止屠宰和断刑等活动、建道场举行斋醮活动、官府赐宴、京城张灯一晚等等内容。[18]当然,这些内容和近代国家的国庆节一般的活动内容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现代国庆节的一般内容,包括官方的各种仪式,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仪式化的剧情再现,阅兵以及其它的庆祝和纪念活动,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大众可以参与的文艺表演等等,[19]虽然具体的作法不一样,但两者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
因此,从其形式来看,开基节不仅仅是“古无是也”,而是相当的“现代”。但显得颇为另类的开基节,在宋代仍然被纳入到五礼的嘉礼之中,可见在宋代的礼制系统中,开基节并没有脱离传统的礼制结构,那么开基节为什么会被纳入到“嘉礼”这一经典礼制的类别之中呢?开基节归属于嘉礼,对于古典礼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古典礼制的经典著作《周礼》对嘉礼的阐释是“以嘉礼亲万民”,
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亲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20]
按照经典注疏的解释,嘉礼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因人心之善者而为之制”,即嘉礼的内容大多是人们喜欢参与的带有喜庆性质的活动。二是嘉礼的施行对象是“万民”,五礼中,其余四礼都针对的是“邦国”,只有嘉礼针对的是万民,因为“万民所行者多”,换句话说,嘉礼本身带有较强的群众性和公共性。[21]这或许能够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开基节会被纳入到嘉礼的结构之中。嘉礼虽然在儒家经典中被分为六大类型,分别为:饮食之礼、昏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和贺庆之礼。但这只是理想的设计,在后世王朝实际运行的五礼体系中,嘉礼基本上被定位为颇有喜庆气氛的“庆典”型的礼仪,以唐代的《开元礼》为例,嘉礼主要包括了皇帝、皇太子、亲王等加元服、纳后、纳妃等,皇帝、太子、诸王接受群臣朝拜等,以及册命皇后、皇太子以及诸王、大臣等,此还有一些对公共文化生活场景的礼仪安排,如乡饮酒礼、宣赦书仪等。[22]这些礼仪的庆典性质,跟后世“节日”活动有许多共通的因素,而“特殊的日子”虽然不是嘉礼的内容,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参数,许多庆典性的礼仪都需要“选择”好的日子来进行,以致于《开元礼》在序例中专门列出“卜日礼”和“筮日礼”,即选择相应的吉日来举行相应的典礼,如皇帝加元服的第一步就是卜日,所以时间选择对于嘉礼而言也是重要的。但“卜日”这种时间选择,在本质上和“开基节”这样的节日非常不同,它不具有稳定的周期性纪念和庆祝的意义,卜日的时间特点不是确定的,“若上旬不吉即卜中旬,中旬不吉即卜下旬”,特定的日历日期本身无法成为礼仪活动的意义,它只有被凶吉占卜术之类的被赋予了另外一套知识力量后才有意义。
因此宋代以前,像开基节这样的具有周期性的,且有着固定的日期的日历日期式的庆典在传统礼制中只有季节性变化的节气时间,如冬至祭昊天上帝、元日冬至行朝贺礼等等,这些时间虽然也有周期性,但都是自然界的季节运行的周期性,体现的是对自然时间的敬畏,和开基节之类的日历日期上的周期性纪念日不同。当然,嘉礼传统中,对自然节气的周期性时间的重视也是存在的,比如“读时令”就在嘉礼中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从东汉开始,由“太史每岁上其年历”,然后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等重要的节气时间点,“常读五时令”。[23]读时令,是在特定的日期定期举行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礼仪活动,比东汉的读五时令的仪制为“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座,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24]
但正如前面所揭示的那样,传统嘉礼中的日期,跟开基节等节日的日期的意义是不同的,开基节等节日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变得伟大,变得有意义。汉唐礼制中,时间在礼仪活动中虽然在场,但却不是主角,礼仪的设计与运行虽然与时间有关,但确认并固定一个人事活动的特殊日期来进行特别的礼仪活动,把时间变成礼的对象本身,并不在经典礼制的设计范围之内。而且那怕是读时令这样的礼仪,实际上也在经典礼制著作中找不到明确的依据,后来唐代也有读时令的礼仪,武则天时代还进一步制订了“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的仪制。但读时令的礼仪活动,却一直以来找不到经典的理论依据,以致于读时令的礼事活动也遭到“非古制也”的批评。[25]
尽管读时令在诸如《周礼》、《礼记》等经典著作中不见记载,但它还是在嘉礼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可见,王朝礼制在后世不断因应世事之需而增益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基节的出现,更是超越了“读时令”,而对嘉礼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质的突破。因为读时令是对春夏秋冬这样的自然时间的肯定,而开基节是对王朝开国、奠定基业的人事时间的选择,这是嘉礼设计的时间选择从自然时间的“节气”到人事时间的“节日”的转向。经典礼制本来就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大环境中,对于自然时间,特别是季节性时间的节气有着很高的敏感度,但对于人事活动的时间坐标的纪念性的敏感度则并不高,开基节实际上是相对于自然时间的人事时间,它把庆典和特定的日历日期结合起来,周期性的复活重要日期的历史意义,它在宋代的出现,有着非常深广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在《宋史》的“礼志”成书以前,包括开基节在内的各种节日(诸庆节)在五礼体系中的官方地位其实是不明晰的。从仁宗时期编修的《太常因革礼》到徽宗时期的《政和五礼新仪》,再到孝宗时期完成的《中兴礼书》,这些宋朝官方颁布的官修礼典中都没有收录“庆节”的内容。虽然如此 ,但“庆节”成为宋代礼典的重要内容,在《宋会要》中是有鲜明的体现的,只不是因为完整的《宋会要》已不可见,现存的重辑的《宋会要》在结构上事实上是凌乱的,体现不出清晰的五礼体系,但《宋史·礼志》把庆节安排到“嘉礼”之中,恐怕也不是《宋史》编纂者的一时兴之所致。
前揭叙述开基节的《宋史》的礼志部分的“嘉礼三”,实际上包含了对两个方面的“节日”礼仪的规定,一是开基节所属的“庆节”,一是比“庆节”历史稍微悠久一点的“圣节”。这样的安排和现存的《宋会要辑稿》的编排是一样的,现存的《宋会要辑稿》也是在叙述完礼典中的各皇帝生日的“圣节”以后,接着记载了包括开基节在内的宋代的各种国家性节日的来历与仪式规定,《宋史·礼志》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反映的是宋人的普遍观感。宋人一般认为,圣节起源于唐玄宗的千秋节,王明清就曾经引唐明皇《实录》关于千秋节的记载,认为“诞日建节,盖肇于此。”[26]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宋人把本朝的礼制及其观念投射到唐代的一种不准确地“观感”罢了,实际上并不能把唐代的千秋节之类的给皇帝过生日的活动和宋代的圣节划上等号,实际上把庆祝生日这种皇帝的个人行为变成礼制化的圣节,也是宋人的发明。[27]而在宋代官修礼典中,“圣节”已经是嘉礼的重要内容,如南宋中期编成的《中兴礼书》的“嘉礼部分”,虽然不见诸庆节的踪影,但高宗的“天申节”和孝宗的“会庆节”等圣节则已经有了详细的叙述,算是纳入到了官方承认的嘉礼的礼典之中了。[28]
二、开基节溯源:天书封祀与真宗朝国家性纪念节日的形成
读时令以及告朔之礼,虽然并不符合经典礼学的规范,但礼学传统对于自然时间重视却是其底色,驳议告朔之礼的司礼博士辟闾仁谞也援引了《礼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和《周礼》“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的说法,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时间与礼仪之间的关联性和重要性,只是他认为有些人对经典礼学的理解有误罢了,他的意见是所谓“每月告朔者,乃诸侯之礼也”,“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29]另一方面,读时令以及告朔之礼的礼学合法性有争议,但这一礼制的施行却具在时间上拥有极长的生命力,从东汉开始,一直沿续下来,因为自然时间的重要性具有普遍意义,自然获得各朝各代的尊奉。但开基节的时间选择,却不再是时令之类的“节气”,而是由政治权力设定和以政治力量为主体去参与和庆祝的节日。
开基节的正月四日的重要性实际上并不具有时间上的穿透力,它之所以重要,其实只与宋朝有关,因为它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日子,是王朝基业的开始。有意思的是,政治性的节日不断涌现,在宋代成为一个全新的现象,魏华仙早前已经注意到,宋代的“庆节”众多,且与传统的民俗节日、宗教节日不同,庆节日期的选择,是朝廷运用政治权力把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的发生日确定为节日,并进行相应的庆祝活动。这是宋代所特有的一种节日类型。[30]宋代包括开基节在内的各种庆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政治力量对经典礼制的“扭曲”,因为开基节的重要性,主要是从王朝政治的角度来观察的,但如果从礼学经典内部来看的话,它的产生找不到任何理论来源,也就是说,开基节的合法性来源,体现的是政治权力战胜了以礼学传统为代表的知识权力,在这里,连像读时令和告朔那样的“误会”的空间都没有。因此,上述的开基节兴起的政治动力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上述观察无法解释开基节出现的时间节点,即它不是出现在王朝建立之后不久,反而是产生在北宋亡国之际。
与近代以来的“国庆节”问题的提出非常不同的是,纪念和庆祝“大宋”开国功成之日的开基节,并不是在开国功成之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民国的国庆节“双十节”的提出,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就确立下来的,当年9月北京临时政府向临时参议院提交《国庆日及纪念日咨询案》,9月24日临时参议院在第80次会议上通过提案,并以临时大总统令的形式于9月29日正式公布。[31]但宋朝的开基节问题,在整个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被人提及,开基节被宋朝君臣提上议事日程的时间,比起近代以来的“国庆节”的认定,则显得相当的滞后,诸书所记,宋廷正式下诏确立开基节已是宋徽宗在位的后期了。
史籍所记宋廷确认正月四日作为一个法定的新的“庆节”(开基节)的具体时间,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宣和二年,另一种是政和二年。政和二年说出自王明清的《挥麈录》。[32]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是在宣和二年(1120年)四月十九日徽宗批复太常寺的“乞将每年正月四日,依降圣节体例立一节名”的申请,正式下“诏以开基节为名”[33]。此外,《皇宋十朝纲要》则记载:宣和二年四月己丑(十八日)[34],“诏以正月四日为开基节”。[35]《会要》与《纲要》编写之时的史料来源可能不一致,但都指向宣和二年,且前后相差仅一天,应当更接近实情。而《挥麈录》作为王明清私人的闻见记录,难免会有记忆失误的时候,所以宣和二年说更值得采信。
开基节问题被提上宋朝的议事日程,目前的史料虽然不多,但结合《会要》和《挥麈录》,其经过大体是可以“复原”的。《会要》记载:
宣和二年四月十九日,太常寺言:“应天府鸿庆宫系圣朝兴王之地,乞将每年正月四日,依降圣节体例立一节名。”诏以开基节为名。[36]
《挥麈录》的记载如下:
因考建中以后诏旨,政和二年南京鸿庆宫道士孟若蒙进状言:“本宫每遇正月初四日为创业之日,修设斋醮,乞置节名,以永崇奉。”诏从其请。[37]
结合这两段史料的叙事,可知开基节的发起,来自于南京应天府的一个道观——鸿庆宫,《挥麈录》所说起因在于该道观的道士“孟若蒙”向朝廷递上了“乞置节名”的“进状”,至于《会要》所记由太常寺“言”,乃因太常寺是相关主管部门,该机构下属的“太社局”,正是“掌讨论大庆典礼、神祠道释加封”等事务的,[38]所以最后才由太常寺将正月四日建立节名的提议上报给皇帝的。从史料中揭示的开基节兴起的背景来看,开基节的“成立”,虽然最后是政治权力加以承认才得以成功,但其缘起,其实并不是完全政治力量主导的结果。
鸿庆宫位于南京庆天府,“睢阳奥壤,艺祖旧邦”,[39]所在之地本就跟宋朝开基事业的标志性象征息息相关,“宋”之国号,即从太祖所领的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即在应天府)而来,这就是所谓的应天府鸿庆宫系圣朝兴王之地的来历。因此,最后由鸿庆宫的道士来推动建立“开基节”,似非偶然。从道士孟若蒙的“进状”来看,每年正月四日举行一些仪式来纪念宋太祖的创业之功,似乎是鸿庆宫的传统,不过这些仪式大体属于道教的宗教仪轨内容,并不在儒家经典礼制的设计之内,也即孟若蒙自己所说的每年正月四日为纪念创业之日,所做的活动不过是在道观中“修设斋醮”而已,斋醮科仪是道教特有的宗教仪式,本来并不在经典的礼制内容之内。但自宋真宗大搞天书封禅以来,推崇道教不遗余力,许多道教仪式早已渗透到经典礼制系统中了。已有学者指出宋代礼制对道教的吸收是全方位的,从礼典到实践,从普通的祈拜到含有政治意图的禀告,都有道教仪式的身影,而五礼体系中,除军礼外,道教也积极融入了吉、嘉、宾、凶四礼的相关仪式中。[40]
其实,比起道教仪式对经典礼制的吉礼的渗透,道教对嘉礼部分的影响实际更大,开基节在道教宫观中“起源”,其实有着深湛的唐宋时期嘉礼变革的进路,真宗时期的崇道之风给经典礼制带来的最大突破,正是一系列的“古无是也”的“庆节”的出现。真宗时代,除了澶渊之盟以外,天书下降可谓是又一影响深远的国家大事,真宗依靠天书带来的神圣性取得泰山封禅的合法性,形塑了真宗朝政治的最大特色。景德四年十一月王钦若与真宗的对话讨论如何“镇服四海,夸示戎狄”时提出,可以通过制造“天瑞”来获得封禅的合法性,并且用“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来引导真宗可以在儒家经典文化之外,去寻求王朝的神圣性和合法性。[41]
这其中“天书”与道教的关系最为密切,天书下降闹剧,在儒家经典文化中实在找不到神圣来源,真宗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神道设教”来弥补这一缺陷。真宗君臣操作的天书下降过程,基本上是以道教的文化资源来加持其神圣性的,大中祥符元年真宗自述的预告天书下降的“神人”,是“星冠绛衣”的道教神仙打扮,神人要求真宗“于正殿建黄籙道场一月”准备接受天书,真宗于是“自十二月朔,即蔬食斋戒于正殿,依道门科仪结彩坛九级,建道场以佇神贶”,[42]整个过程采用了说法和做法都是道教的,如果站在儒家立场,那完全是“怪力乱神”的昏招,天书并不拥有神圣性,更不能为真宗粉饰盛世提供合法性。天书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完全来自于本来跟宋朝皇室没有多少关系的道教。
宋代第一个“庆节”即是在第一次天书下降后的当年设立的,《宋会要》记载: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两京诸路州、府、军、监前七日选道流于长吏廨宇或择宫观建道场设醮,所须之物并从官给,仍令三司降例。其月已断屠宰,更不处分。节日臣僚士庶特令宴乐,其夕京师燃灯,著在令式。[43]
天庆节的设立,可以说是真宗对天书下降的纪念和庆祝,真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下诏设立一个前所未有的“节日”呢?当年正月三日,天书下降以后,真宗获得了“上天”的认可,拥有了超凡的神圣性,从而取得了泰山封禅的资格,将大宋盛世推向了高潮,当年三月,“诸道贡举人”共计“八百四十六人伏阙下请封禅”[44],接着在四月一日,“天书又降”,然后在宰相王旦领衔下,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蕃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共请封禅。真宗于是下诏“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正式确定了泰山封禅之事。[45]最后,真宗的封禅活动在十一月全部完成,当月丁丑日回到开封,六天后的“壬午”日就正式下诏设立“天庆节”。[46]
天庆节正是对传统礼制的“偏离”,天庆节的深层基础来自于真宗的道教实践及其斋醮仪式的连续体验,它的设立完全冲破了儒家礼制的框架,天庆节的行为和观念,本不在经典礼制的关怀之中,而无论是设立的根据——天书下降,还是相关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建道场设醮、禁屠宰等,都带有强烈的道教科醮仪式的内容,天庆节似乎更像一场道教的集体欢狂,与儒家的礼学体系格格不入。魏华仙此前已经注意到,真宗时期所有的“庆节”几乎都跟天书下降有关,是对真宗营建出来的盛世的表彰,她认为真宗要把那些有着重大意义的时间留住,使其年复一年、持续不断地传承朝廷的方针策略的最好办法,就是设立节日。而真宗朝的出现的五个全新的节日——天庆节、天贶节、先天节、降圣节、天祯节(分别是天书第一次下降于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天书下降于泰山、圣祖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以及天书第二次降于大内功德阁),[47]政治用意非常明显,政治功能也十分清晰。看起来宋代各种“庆节”的起源,似乎只是天书下降的“副产品”。
天庆节是第一个依据王朝政治意义的重要性来设定的纪念日和庆祝日,这一点跟“开基节”是一样的,可以说开基节的真正起源正是天庆节。天庆节的设立,其实是对真宗君臣制造的“泰山封禅”的盛世象征的纪念和庆祝,从泰山回来,真宗帮大宋在没有汉、唐那样的“武功”的情况下,实现了汉、唐一般的盛世伟业,对于大宋王朝来说,这虽然不是“开国”,却是非常了不起的“功成”,的确值得纪念和庆祝,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庆节就是大宋的“国庆节”,因为封禅的合法性,来自于“天书”,在整个封禅活动中,天书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真宗得到上天认可的标志,封禅的过程中,“天书”都有豪华的仪卫队护持,到封禅时,由“仪卫使奉天书于上帝之左”,[48]作为封禅的凭证,所以,没有天书的下降,就没有泰山封禅的举行,更没有后来的祀后土于汾阴,朝谒老子于上清宫等等大型的政治文化活动。所以天庆节名义上纪念天书下降,实际上是向世人宣示封禅泰山的伟大盛世的来临,是真宗对自己一手操办出来的伟大时代的周期性的举国欢庆,封禅只能表演一次,但天庆节却可以每年都过。
真宗时期“诸庆节”的出现,当然具有极强的政治目的,这些庆节也自然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功能,但诸庆节的设立,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最难的是对礼制的突破,它把具有重要政治文化意义的纪念性的人事时间本身变成了礼仪活动的主体内容,也即在传统的嘉礼结构中为“庆节”的增加新的空间。庆节这种法定的节假日举行的庆典,补充甚至是替代了传统的嘉礼“亲万民”的功用,传统的嘉礼中虽然也有许多“庆典”式的内容,但却缺乏一种“节日”狂欢的类型,缺乏一种对激动人心的日子和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本身的赞颂,事实上在经典礼制的设计理念中,因为考虑到嘉礼的内容,“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设礼节以裁制之”[49],显然,嘉礼虽然处理的是庆典类的礼仪设计,但其关注的重心却不是要在庆典仪式上如何发挥集体狂欢的功效,恰恰相反,它正是要以儒家正道的庄严肃穆的克制去消解大众在高兴的事情上有可能出现的过度地喜气洋洋的放纵。
道教的走红,给宋朝君臣在礼制建设方面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突破的契机,实际上由于道教本土宗教属性,它本来就很容易渗透到传统礼制之中,唐代在玄宗崇道高潮时期,玄宗泰山封禅的仪制就夹杂了大量的道教科醮仪式,而《开元礼》的吉礼中,有不少实为道教的内容和观念,但却用儒家的传统礼制的名义进行了包装,特别是在祭祀过程中对荦血气味的剔除。而唐玄宗为自己生日设置的“千秋节”,“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实际上是对道教的得道成仙的理想的追求的仪式化,虽然它被纳入到“嘉礼”之中(《开元礼》中有《嘉礼·皇帝千秋节御楼受群臣朝贺》),但实际上是以儒家传统礼制面目出现的道教内容。[50]真宗时期以天庆节为首为五大庆节,代表着皇权意志利用道教文化资源对传统礼制的突破,以及道教仪式对传统礼制的补充,这正是《宋史》礼志所谓的“诸庆节,古无是也,真宗以后始有之”[51]的意义所在。可以说,真宗朝确立的五个庆节,把道教的科醮仪式与王朝的节日设置连接了起来,即一种新的礼仪的确立,可以不需要从儒家经典礼制中寻找其合法性,皇权本身就是“礼制建设”的合法性。事实上天庆节等节日的“著在令式”,以诏书的方式公布,以令和式的形式运行,是以法定的节假日的形态出现的,与其说最初它是礼典的内容,还不如说是法典的内容,《庆元条法事类》中就有关于天庆节、开基节等节日的禁屠令。[52]
三、开基节的产生:礼崩乐坏与自下而上的节日创造冲动
宋徽宗宣和二年,开基节以诏令的形式正式确认,当然离不开前述真宗开创的节日创置传统,但真宗以后,宋代的节日创造冲动就嘎然而止了,从仁宗到哲宗,朝廷一直没有设立新的庆节,而且旧的庆节的庆祝力度也大大降低,仁宗即位后,朝廷获取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方法渐渐回归儒家传统,道教色彩浓厚的天庆节等五大庆节的庆祝活动的规模也受到抑制。[53]直到徽宗后期新的崇道高潮到来,新的庆节创置才重新出现,而开基节正好就是产生在徽宗后期的崇道高潮中的。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政和四年(1114年)正月,在庆节创置停止了将近百年之后,徽宗下诏设立了第一个新的节日——天应节:
徽宗政和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诏曰:“朕修祀事,荷帝溥临,旌旗、辇略、冠服、仗卫见于云际,万众咸睹。可以十一月五日为天应节。[54]
天应节设置的起源,是为了纪念和庆祝一个所谓的仙人降临的神异事件,徽宗在政和三年(1113年)十一月举行了一次南郊大典,在这次南郊中,出现了所谓的“天真示见”[55]的盛事,详情如下:
上搢大圭,执玄圭,以道士百人执仪卫前导。蔡攸为执绥官,玉辂出南熏门,至玉津园,上曰:“有楼殿重复,是何处也?”攸即奏,见云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皆去地数丈。顷之,上又曰:“见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衣服眉目,历历可识。攸遂请付史馆。[56]
徽宗与蔡攸自导自演的“天真示见”的闹剧,与真宗群臣当年颇有几分相似。按《宋史》所记,这次南郊,乃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57],“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乃是“岁之大祀”,[58]即吉礼中最重大的祀典,冬至祀昊天上帝,因为在万物收成之后,意在报上天生成万物之功,所以礼制最为隆重,而徽宗的这次南郊,在礼仪上更加的道教化,不但“以道士百人执仪卫前导”,而所谓的天真示见的场景,也完全是道教神仙下凡的样子,儒家敬天的象征昊天上帝的形象几乎要被弄成是道教神仙了,可以说完全偏离了儒家经典中的礼制传统。昊天上帝的地位在儒家礼制系统中为最高级的神祇,但宋代道教实际上也把昊天上帝纳入到道教神仙系统之中的,而且其地位在道教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和太上老君之下,道教的这一神仙座次,曾遭到宋代大儒们的批评,朱熹就曾非常激动地说“昊天上帝反坐其(三清)下,悖戾僭逆,莫此为甚”。[59]
值得注意的是,跟真宗时代的节日创置一样,徽宗时代新设立的以天应节为首的系列庆节(除天应节外,徽宗时期设置的类似的“庆节”还有宁贶节、天符节等),大多遵循着真宗时代形成的一套节日生成的传统,即朝廷以事后追认的形式,把带有强烈的道教色彩的神异事件的出现,以及以这些神异事件为依据举行的重要活动所发生的特殊时间(日期)确认为一个新的“庆节”,然而,开基节的设立,显然并不符合这一庆节创置的传统,它既没有在当朝皇帝统治之下出现的某种神异或显灵事件,也不是当朝皇帝借助神力而主导的重大政治活动。如果说天应节至少在表面上仍然符合真宗时代的庆节创置传统的话,徽宗后期的一系列新建的新节日则完全突破了真宗的套路。真宗借助道教思想资源和仪式来解决儒家传统思想的在礼制建设上的短板,把庆节引入到嘉礼建设之中,虽然有道教力量的参与,但却并不是一个道教的活动,而是王朝神圣性和合法性设计的重大政治活动。但徽宗后期,庆节的设置实际上已经成为王朝末世乱政的象征,最有代表性的是宣和元年“天符节”的设置:
宣和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散郎、知制诰、兼侍读王安中言:”闻日者孟冬癸卯,屈万乘之尊,以玉清神霄华琼室禁经秘箓传受成赐开度,又以仲冬乙卯开宝箓大陈法会。欲望以其日依天宁、天贶例,制名纪节。”诏以其日为天符节。[60]
天符节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五日”,[61]即王安中所说的孟冬癸卯,这一天,徽宗“御宝箓宫,传度玉清神霄秘箓,会者八百人。”[62]所谓“玉清神霄”之说,为徽宗后期最宠信的道士林灵素的“发明”:
天有九霄,而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63]
玉清神霄说正是林灵素为徽宗提供的新的神圣性论证,然而在时人看来,林灵素的得宠,正是徽宗末年怪力乱神政治的高潮,既便是从道教本身的角度来看,林灵素也是道流中的末流,在时人看来,他不过是“务以欺世惑众,其说妄诞,不可究质,实无所能解”,徽宗虽然对林灵素尊崇备至,但林在讲道时的表现,却是“所言无殊异,时时杂捷给嘲诙以资媟笑”罢了。[64]在徽宗眼中最杰出的道士代表林灵素的宗教能力和素质,却实在是难入世人的法眼,如此反讽的效果,更增添了国之将亡,必有怪力乱神兴风作浪的妖氛。如果说真宗时代的庆节设置,是从道教神仙体系中为皇权神圣性的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的话,徽宗时代的天符节的创设,已陷入到末世来临的怪力乱神的狂欢之中。跟徽宗比起来,真宗当年的“神道设教”的种种行为,反倒显得特别地“清醒”。[65]
事实上,真宗时代所设置的五个庆节,虽然在礼仪上和礼制建设的观念上都具有强烈的道教色彩,但是真宗的崇道只不过是因为无法从儒家传统思想资源去中为自己的“东封西祀”的所谓功业,去寻找合法性的无奈之举,仔细考察真宗对道教本身的态度,恐怕不存在虔诚的信仰的,更没有疯狂的迷恋,他只不过是利用道教来突破传统儒家礼制系统的政治文化的束缚罢了,事实上有学者已经看到真宗崇道背后的“国际”文化竞争的意味。[66]真宗时代的崇道活动,其整个过程的节奏完全掌握在真宗及其亲信大臣一方,可以说真宗时代,道士群体的主动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在真宗时代的诸庆节的建立过程中,道士常常是背景式的道具,起着“陪位”的作用,而徽宗朝的道士已在王朝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既是徽宗崇道活动的导演,也是崇道场景中的主演,可谓人才辈出,争奇斗艳。[67]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开基节产生的背景,它不是像真宗时代的天庆节那样,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由应天府鸿庆宫道士发起的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林灵素的成功,让道士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遂立道学,置郎、大夫十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68]如此众多的职位和晋升空间提供给了道士群体,无形中必然激发天下道流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开基节即是在这样的背景出中出现,可以说是身在基层的道士孟若蒙独具慧眼的“发现”。孟若蒙在南宋初年曾经与王明清有所来往,王自述其“作南京少尹日,尝与之(孟若蒙)游”,据王朝清观察,孟是一个相当聪明且有进取心的人,他不但“亦能诗文”,是个小有才华的道士,而且在绍兴年间,“又以前绩自陈”,显然试图争取朝廷对他有较好的安排。[69]可见当年促使他建议开基节的创设的,正是不甘寂寞地从基层揣摩上意以求在高层有所表现的上进心。
另一方面,从《会要》所录鸿庆宫的建节申请“本宫每遇正月初四日为创业之日,修设斋醮,乞置节名,以永崇奉”来看,考虑到鸿庆宫的建置来自于它“睢阳奥壤,艺祖旧邦”的地位,作为太祖的潜藩之地的道观——鸿庆宫,该道观对正月四日的关注,正月初四在观中举行斋醮仪式,只是作为艺祖旧邦的一个崇奉太祖的习惯性的宗教仪式,或者说正月四日的重要性,恐怕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大宋王朝境内所有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只不过是鸿庆宫作为太祖兴王之地的常规动作。按《宋史》所说,开基节的主要活动是“正月四日有太祖神御之州府宫殿行香”,[70]《宋会要》的说法也是“在京合于景灵宫皇武殿、州军于有太祖皇帝神御处烧香”。 [71]行香和烧香其实都不是经典礼制的作法,而开基节纪念仪式举行的地点,是有太祖御容画像的地方,可见开基节与太祖的紧密关系。而对祖宗御容的朝拜,后来也发展成为开基节活动的重要内容,南宋末年马端临曾撰文记述了在拱极堂“摹成四轴”祖宗御容,然后施行“每以岁之开基节恭行朝拜礼”的纪念活动。[72]
一方面,一个道观的行为可以上升到国家礼制建设的层面,这是真宗以来形成的新礼制传统。但另一方面,更要的是,这时的形势大约使道观和道士们有了创造新“庆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开基节这个看起来跟大宋王朝关系最密切的节日,似乎却是惟一一个不是由朝廷主导设计的节日。如果说宋代庆节的出现,是对经典礼制的偏离,那么开基节的出现,则又是对庆节传统的偏离,那么从礼制意义上讲,颇有些反讽意味的是,在北宋末年出现的这个纪念王朝开国功成之日的开基节恰是大宋王朝礼崩乐坏的象征。因为如非徽宗时代的制礼作乐走上了邪路,恐怕根本不会有创造开基节的冲动。
徽宗时代实际上花了很多功夫大力制礼作乐,意图营造盛世,但这些礼乐成果在南宋士人看来,大多荒诞不经,有违正统礼制的精神。早在崇宁年间,朝廷“协考钟律”时,道士魏汉津向徽宗提出“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而中指之径围,则度量权衡所自出”的“迂怪”的音律理论,开启了北宋末年“乐坏”的进程。[73]而在礼制建设方面,徽宗时代虽然编成了卷帧浩繁的《政和五礼新仪》,但却颇受正统儒家士大夫的批评,朱熹就曾议论说:“政和间修五礼,一时奸邪以私智损益,疏略抵牾,更没理会。”[74]显然,在后人看来,徽宗时代的礼制设计,已经被奸人带上了邪路,高宗即位后,对徽宗留下来的庞大的礼制遗产,实际上心情复杂,反映在如何处置徽宗新创设的包括开基节在内的系列庆节的问题上,高宗的态度值得玩味。
开基节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它的命运其实是有些尴尬的。高宗即位以后,对徽宗时代创置的系列庆节进行过一翻整顿,基本上废止了徽宗时代设立的除开基节以外的其它所有节日,《宋史》在“诸庆节”部分记载:“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五日,诏:政和以来添置诸节,除开基节外,余并依祖宗法。”[75]而《要录》说得更清楚,“诏政和以来诸庆节号真元、宁贶、天成、天符、天应者,皆罢之,惟开基节如故。”[76]显然,在高宗看来,徽宗时代的建节活动是有违祖宗之法的乱政,必须加以清除,但有意思的是,开基节又成了高宗清除节日行动中的例外者。这大概跟开基节名义上纪念太祖开国有关,面对这样的理由,高宗也不宜简单地将其一废了之。何况对高宗而言,鸿庆宫所在的应天府,不但是太祖的兴王之地,也是高宗自己的兴王之地。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高宗以“兵马大元帅、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77],高宗又在应天府开启了南宋的历史,王明清在论述开基节的缘由时就曾感叹高宗后来能够在应天府即位,重建宋朝确属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正是“中兴再造,复在南都,符命岂偶然哉!”[78]这样,开基节到了南宋,仍然沿续了下去,朱熹在《书康节诫子孙文》的文末,落款“淳熙庚子开基节日新安朱熹谨书”,[79]显然在朱熹的时代,开基节这个国家性节日已经以一种特定的日历时期的方式而成为宋人日历上的时间标志。
参考文献
[1]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2]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3] 《国节日效法法美》,《申报》1912年10月1日,第2版。
[4] 哈里森即认为,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一套以国旗、西装、剪辫、放足、西历以及国庆日为象征符号的新型政治文化,从而形塑了中国人的新的国族认同感。参见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关于宋代的“开基节”,学界尚未展开相关的专题研究,但已有学者注意到包括开基节在内的宋代“诸庆节”的问题,并且揭示出宋代的“诸庆节”的官方节日功能,在完善中国古代节日系统结构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参见魏华仙:《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
[6]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诸庆节》,中华书局,1985年,第2680页。
[7]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第4—5页。
[8] [宋]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一《故事》,中华书局,2007年,第33页。
[9] [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前录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0] 据《二十史朔闰表》,当年二月朔为“壬辰”,则甲午当为“初三”,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1页。
[11] [汉]班固撰:《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52页。
[12] 参见[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1030—1033页。
[13] 据《二十史朔闰表》,当年五月朔为“乙巳”,则戊午当为“十四日”,甲子则为二十日。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第83页。
[14] [晋]刘煦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页。
[15]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诸庆节》,第2680页。
[16] 参见李学智:《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
[17]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05页。
[18] 参见魏华仙:《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第436页。
[19] 参见Cina, A. National history as a contested site: The Conquest of Istanbul and Islamist negotiations of the N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01:(2),pp364-391
[2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第十九《大宗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70—674页。
[2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第十九《大宗伯》,第670页。
[22]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六,中华书局,1988年,第1440页。
[23]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十,第1922页。
[24]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十,第1922页。
[25]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十,第1926页。
[26] [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前录卷一,第1页。
[27] 唐代礼制中并没有宋代的圣节,《旧唐书•礼仪志》、《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礼书部分都没有单列出圣节,陈怀宇认为,圣节作为一套完整和正规的政权礼制和礼仪的产生和定型是在宋代。圣节作为庆贺皇帝生日的制度仅在宋代才逐渐确立。详细的论证参见陈怀宇:《礼法、礼制与礼仪:唐宋之际圣节成立史论》,《唐史论丛》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50—279页。
[28] 《中兴礼书》的“嘉礼”三十一至三十六共用了六卷来叙述了天申节和会庆节的各种仪节,参见[清]徐松辑:《中兴礼书》卷二百三至二百九,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第1—55页。
[29]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十,第1923—1924页。
[30] 参见魏华仙:《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
[31] 参见《参议院第80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附录,中华民国元年十月十九日第171号。
[32] [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前录卷一,第3页。
[33]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2005页。
[34] 按当年四月朔为“壬申”,己丑日则为十八日,参见洪金富编著:《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222页。
[35] [宋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十八,中华书局,2013年,第514页。
[36]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2005页。
[37] [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前录卷一,第3页。
[38]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3632页。
[39]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563页。
[40] 参见王志跃:《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以〈宋史·礼志〉为中心的考察》,《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第46—49页。
[41] 参见《长编》卷76,第1506—1507页。
[42]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1896—1897页。
[43]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2000页。
[44]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己卯”,第1529页。
[45]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己卯”,第1531页。
[46] 《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己卯”,第1577—1578页。
[47] 参见魏华仙:魏华仙:《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第435—436页。
[48] 《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己卯”,第1571页。
[49]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第十九《大宗伯》,第670页。
[50] 参见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2—83页。
[51]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诸庆节》,第2680页。
[52] 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九“畜产门”的采捕屠宰的规定,“诸禁屠宰,天庆、先天、降圣、开基节,丁卯、戊子日各一日”。
[53] 魏华仙梳理了仁宗时期朝廷陆续颁布的关于天庆节等五节的新制,总体原则就是降低这些节日的规模,裁减节日期间斋醮的数目,停止节日期间的赐宴,缩短节日期间的禁刑时限,甚至一度取消了节日期间的休假。参见魏华仙:魏华仙:《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第437页。
[54]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2004页。
[55]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诸庆节》,第2681页。
[5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二,第1067页。
[57]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三》,第392页。
[58] 《宋史》卷九十八,第2425页。
[59] 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25《论道教》,中华书局,1986年,第3005页。
[60]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2005页。
[61]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诸庆节》,第2681页。
[62] 《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十八,第508—509页。
[63] 《宋史》卷462《林灵素传》,第13528页。
[64] 《宋史》卷462《林灵素传》,第13528页。
[65] 武清旸的考察揭示,真宗早年对道教并无特别的兴趣,而且天书下降以及相关的道教崇拜活动中,道士群体大多是一个背景式的存在,道士群体中也并无特别显眼的人物参与到真宗的崇道过程中,也基本上没有个别道士这个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参见武清旸:《宋真宗的道教信仰与其崇道政策》,詹石窗主编:《老子学刊》第7辑,巴蜀书社,2016年,第109—116页。
[66] 参见胡小伟:《“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7—16页。
[67] 参见王曾瑜:《宋徽宗时的道士和道官群》,《华中国学》2015年第2期。
[68] 《宋史》卷462《林灵素传》,第13529页。
[69] [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前录卷一,第3页。
[70]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诸庆节》,第2680页。
[71] 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2005页。
[72] 马端临:《碧梧玩芳集》卷13《恭题祖宗御容及从祀功臣下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 参见《宋史》卷462《魏汉津传》,第13526页。
[74]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4《论考礼纲领》,第2182页。
[75]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诸庆节》,第2681页。
[7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第240页。
[77]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中华书局,2013年,第131页。
[78] [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前录卷一,第3页。
[79] 朱熹:《书康节诫子孙文》,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2015年,第4316页。
▼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com
编辑:潘梦斯
1.《【11说宋朝】黄博:“国庆节”的中古起源:嘉礼传统视野下宋代“开基节”研究丨202104-102(总第1642期)》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11说宋朝】黄博:“国庆节”的中古起源:嘉礼传统视野下宋代“开基节”研究丨202104-102(总第1642期)》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359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