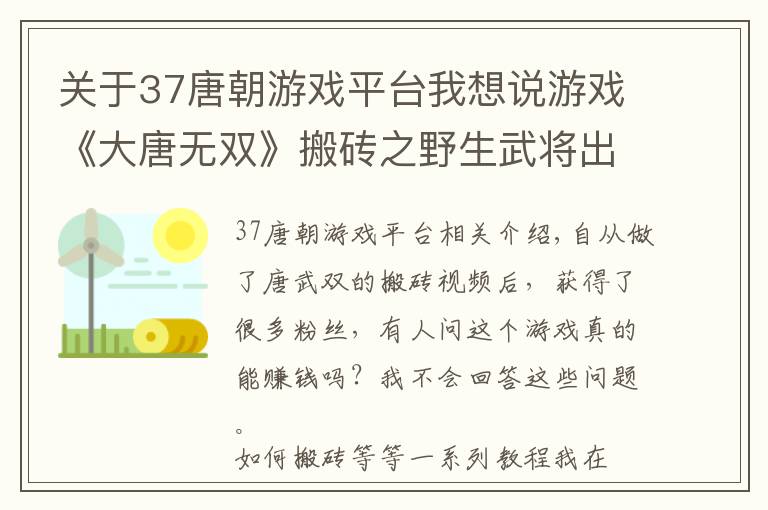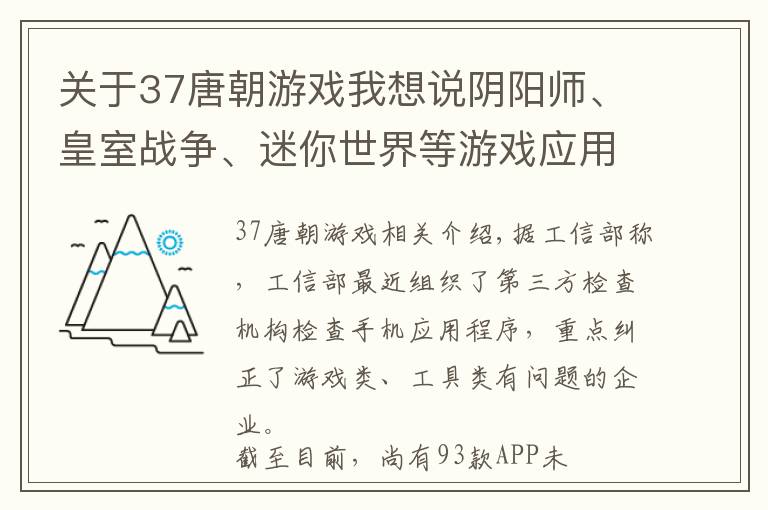编辑
著名党史专家王正平教授解释大唐300年军事外交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中文版最近出版了。
唐王朝在将近两百九十年的统治期间,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突厥、回鹘(原名回纥,788年改为回鹘)、吐蕃及南诏的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公开交战的种种变化。这些政权相继崛起,除了回鹘,其他转而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王贞平教授以“多极”作为研究唐朝复杂外交关系的分析工具,考察了唐与四邻的关系。本文为该书的导论,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标题为编者所拟。亚洲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与相互依存
“多极”就是指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581-618)土崩瓦解,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北方和西北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李渊及其追随者便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渊最终建立了唐朝,但此时他的实力和对手相比并不占优。北方草原上各游牧部落的宗主突厥,同样也是李渊及其对手的宗主。突厥支持或打击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成全或打破其称霸中原的美梦。为了获得突厥的协助和保护,这些相互竞争的地方势力纷纷向突厥统治者称臣。李渊也不例外。
李渊在618年建立唐朝后,未能立即将多极亚洲变成由唐主导的世界。他在位只有八年多,其间致力于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但未能完成任务。直到他的儿子太宗(627-649在位)继位后,唐才在628年铲除了西北最后一股割据势力。
630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整个亚洲都感受到了崛起的唐朝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游牧部落纷纷奉太宗为“天可汗”,许多政权定期向唐廷遣使朝贡,以示效忠。
然而,唐朝与其他政权的君臣关系基本上名大于实。[1]它们看似顺从,却常常设法操纵双边关系。它们设法在唐朝设定的世界秩序之外为自己保留了很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向唐廷称臣纳贡实际上是它们的一种外交策略,目的是自我保护,增强自身实力和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四邻以这样的权宜之计处理与唐的关系,兼顾到了唐和它们自身的利益——在礼仪层面满足了唐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虚荣心,四邻则能够获得实质利益。唐代的朝贡体系因而得以长期维持。[2]
朝贡体系维持了唐朝至高无上的表象,却掩盖了亚洲的多极本质。唐的四邻原来大多是没有文字、社会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与唐接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唐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取得了长足进步。[3]位于东北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位于西南的南诏,均发展为以农耕或半农耕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初步成型的稳定政权。其自身的发展对其与唐朝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政权除了与唐廷往来,彼此之间也有密切联系。[4]亚洲地缘政治因此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层次更多。[5]
亚洲各政权权力关系的特征是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而不是由唐朝主宰。总体来看,从620到750年期间,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在与四邻的实力对比中占优势。相比之下,四邻因制度尚不健全,内斗不止,自然灾害频仍,彼此间冲突不断而处于劣势。[6]但当唐朝和它的某个主要对手均不受内部政治纠纷困扰之时,它们就会转变为对等关系,而且双方各自的野心常常导致边境冲突或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任何一方因内乱或其他原因衰弱,实力天平就会倾斜,双边关系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统一、强盛的唐朝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个深陷内乱而不能自拔的对手;如果唐廷有意,还能强迫对方称臣。反之,一个四分五裂的唐朝会发现自己很难让四邻俯首帖耳。处于弱势地位的唐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让对方称臣,转而以屈辱的姿态与颇具威胁的新对手打交道。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开始由盛转衰。随着战乱的蔓延,唐廷急需借助外部援助化解内部危机。唐在回纥的帮助下最终平定了叛乱,但回纥的介入意味着亚洲各势力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唐廷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对外事务中维持影响力,它的实力仍不可小觑,但已不再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权力中心。此后,唐与吐蕃、南诏的竞争愈演愈烈。实际上,许多政权从不认为自己是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唐朝即便在鼎盛时期也时常不能完全令这些政权的君主听命于己,现在它们则公开与唐为敌。唐在亚洲逐渐被边缘化,很多唐朝大臣却视而不见,假装一切依然故我。不过,尽管情势如此,唐与四邻仍然无可避免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唐廷需要盟友和外部军事援助来解决自身内政、外交难题,而四邻也希望维持与唐朝的文化、经济交往。双方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与对方维持有意义的关系。双方为谋求各自利益,在接触对方之前,都会先务实地评估对方。它们之间的往来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复合相互依赖”的游戏。由于唐与四邻的命运密切相关,“多极”成为亚洲权力关系的显著特征。
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
多极亚洲的复杂性促使各政权——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都必须借助软实力来处理对外事务。软实力是指通过非暴力手段引导出相关各方均能满意的结果的能力。这些手段需要上述各方付出有形和无形的代价。[7]在古代亚洲,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表示政治效忠是其运用软实力的主要方式。初唐统治者就曾以这种方式处理与突厥的关系,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唐朝建立、发展的外部环境。一些亚洲政权在与唐或其他政权交往时也采用了类似策略,目的是创造一个能让它们顺利实行对外政策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政治效忠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对于弱小的政权来说,向强权宣誓效忠不失为一种良策,可以避免与强权发生冲突,获得其军事援助,从双边关系中获取文化、经济利益。不仅如此,这个举措并不简单地使一方成为赢家,另一方成为输家,它是一场能使双方通过不同的方式同时受益的“非零和”游戏。名义上的宗主国可以通过接受朝贡来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的政治声望,而朝贡国则能获得军事援助、保护和物质回报。唐与新罗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最好的实例。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东南,在地理位置上比高句丽和百济距长安更远。高句丽和百济与新罗为敌,时常阻拦新罗派往唐廷的使节,意图干扰新罗通过引进唐朝的文化和制度以自强的计划。但新罗还是设法与唐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关系。新罗在名义上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并苦苦抱怨高句丽和百济阻挡了新罗派往长安的朝贡使。新罗巧妙运用软实力,最终使唐廷相信,在唐征服高句丽的大计中,新罗将是忠实的盟友。唐廷决定支持新罗,介入朝鲜半岛的纷争。唐远征军在660和668年先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新罗面对强大的唐朝,巧妙运用软实力,实现了自身的利益。
“多重效忠”是弱小势力运用软实力的另一种方式。它们夹在区域强权之间,不得不设法限制和平衡对自身威胁最大的势力。为了自保,它们往往审时度势改变效忠对象。最终在云南建立南诏国的南诏部落就是一例。
从七世纪五十年代到710年前后,唐和吐蕃激烈争夺云南地区的控制权。当地主要部落大都站在吐蕃一边。但六大部落——六诏——中实力最弱的南诏却选择坚定不移地支持唐朝。南诏的忠心终于在712年为其带来丰厚的回报,当年第四代南诏首领被唐廷封为“郡王”。他和他的继承人在唐的默许和支持下吞并了其他部落,在735年建立了南诏国。但是,南诏和唐不久之后就反目成仇。南诏企图向云南东部扩张,而该地区已经部分处在唐廷的控制之下。激烈的战事随之而起。南诏君主害怕遭到唐朝的报复,遂在751年与吐蕃结盟。他接受了吐蕃封号,并正式宣布南诏成为吐蕃的一部分。
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软实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由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上层的奢华生活方式。唐廷决定培养其他政权统治阶层对唐朝生活方式的仰慕之情,期望他们能出于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支持与唐廷维持亲密的政治关系。[8]为达到这个目的,唐廷允许在长安的外国使节或地方政权的朝贡使接触唐文化。他们能够得到汉文典籍,前往国子监观摩儒学讲授,在市场购物,参加国宴、新年聚会、皇帝诞辰庆典等盛大的宫廷活动。不仅是外国使节,其他外国人也有机会体验唐朝博大丰富的文化、物质生活。经唐廷批准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僧侣、留学生可以在中国长期停留,学习各种知识,融入中国的生活。外国商人则可以在首都、边境市场或港口经商。
唐朝独特的软实力在亚洲受众很广,对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日本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变革性影响。它们效仿唐朝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言,将唐朝的许多因素植入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之中。甚至连一些游牧、半游牧社会的统治者和知识界、政界精英也受唐朝软实力影响,渐染华风。[9]唐与四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文化隔阂。
然而,四邻虽然推崇、引进、吸收唐朝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却未必因此在政治上服从唐朝或支持唐的地缘政治目标。借鉴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只是一些政权推进自身体制建构的手段,一些从唐朝引进的观念还常常唤醒或强化了其他政权统治者自身的政治意识。例如,唐廷常以华夷观念为自己的对外政策辩护。其他政权的一些君主不仅拒绝承认唐廷的这一论调,还发展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否定了唐廷设想的以唐朝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上述意识形态发端于四世纪末至六世纪末。当时一些游牧部落占领了华北,并建立了几个区域性政权。[10]大致在同一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11]日本[12]也开始了争取地方统一的历史进程。以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应运而生。这是由于竞逐霸权的各方都需要借助“权力中心论”来证明自身权力的正统性,以彰显自己相较其他竞争对手的优越性。以高句丽为例,它在四世纪初开始扩张,至五世纪末,其势力范围已经涵盖朝鲜半岛北部、百济、新罗、扶余(位于松花江流域)和肃慎(位于今中国东北)。414年为高句丽君主和受命统治扶余的高句丽官员竖立的石碑上,刻有“恩洽于皇天”“恩养普覆”“天下四方”等体现“权力中心论”的字句。[13]此外,在“权力中心论”的引导下,一些政权视四邻为事实上或想象中的“属国”,构建起自己的“小帝国”。新罗即为一例。虽然它对日本和渤海国都没有实际控制权,但还是视其为自己的属国。[14]
“权力中心论”对这些政权的对外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拒绝对唐言听计从,与唐的来往也主要是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例如,初唐时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虽然向唐遣使纳贡,接受唐朝册封,但其真实意图是在朝鲜半岛争夺霸权时赢得唐朝的支持。他们从未在言辞上对唐的天下秩序表示异议,但绝不会执行任何有损自身利益的唐廷指令。新罗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成为朝鲜半岛的霸主之后,随即反对唐军继续在半岛驻扎,但同时依然维持着与唐的外交关系。新罗多次遣使赴唐,寻求机会加强文化联系,保持贸易往来。位于中国东北的渤海国曾一度与唐为敌,并在数十年间向突厥称臣纳贡。它后来恢复了自主地位,唐廷没有质疑,并与之建立了正常的外交、文化和经济联系。在日本,国家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促使日廷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摆脱唐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日本也与朝鲜半岛的邻居一样,将国家利益置于国家意识之上,避免公开挑战唐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在与唐交往时,试图把双边关系的政治、文化、经济层面区分开。为了保持政治独立,日廷巧妙运用外交辞令,淡化了呈递给唐廷国书的“中国中心论”色彩。尽管如此,日本并不想损害与唐朝的官方关系,而要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关系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15]更有甚者,突厥、回鹘、吐蕃和南诏等强邻都曾要求唐朝不得以“属国”对待它们,而唐出于不得已,有时只能在交往中与它们平起平坐。
由此可见,文化、制度的借鉴是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唐试图利用文化吸引力影响四邻的对唐政策,而四邻作为文化的吸收者,则根据自身情况对从唐朝输入的观念加以改造,形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理念,抗拒唐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16]四邻以自身的“权力中心论”为荣之时,就是唐廷丧失国际秩序话语垄断权之日。唐的追随者越来越少。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唐朝是亚洲大陆的权力中心,此后却风光不再。亚洲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硬实力及其局限性
新近崛起的亚洲强权总是力图改变亚洲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现状。它们要求改变与唐的关系,以反映其对唐的新立场。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或运用审慎、和平的手段,或直接诉诸武力。唐廷面对拒不听命或抱有敌意的外国君主和地方政权首领,有时会使用硬实力,包括以武力威胁和直接出兵征讨两种方法。若是前者,唐廷会召见外国君主、地方政权首领或是他们的使者,要求其在朝见时解释自己的逾矩行为。这种情况下的朝见其实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胁迫手段,目的是对外国君主或地方政权首领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改弦更张,继续对唐朝贡,否则唐有可能会对其发动惩罚性的军事行动。
武力固然是国际政治的固有要素,但唐在真正诉诸武力阻止不利于己的国际事态发展之前,必须首先仔细考虑一些棘手问题:唐是否拥有足够资源发动、赢得战争?在战事初步告捷之后,唐军能否有效控制并最终将对手的领土纳入唐朝版图?如若不然,唐廷能否扶植一位本地傀儡,委托他代行统治权?事实上,唐廷官员需要对这些问题反复斟酌,恰恰说明仅依靠“硬实力”处理双边问题有明显的局限性。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但不会一劳永逸地圆满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唐远征军带来难以应付的新难题。在新近获得的土地上重建、维持秩序,是一项耗时耗力的艰巨任务,唐廷及其军队对此往往缺乏足够的准备。唐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便是一例。
唐代战略思维的新视野:实用多元主义
在多极世界中,直接以武力处理对外关系收效有限,而以软实力解决相关问题则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唐廷官员因此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战略。他们将“知己知彼”作为首要原则,以反映唐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想象而不是理解四邻,认为四邻不是敌视中原王朝的价值观,就是对其不屑一顾;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成一出道德剧,舞台上只有拥护或反对中原王朝两种角色。
唐朝君臣在审视对外关系时,试图跨越文化隔阂,不带道德偏见地看待事实。高祖和太宗最先摒弃了对突厥的刻板印象。他们在了解了突厥的政治制度、各部首领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后意识到,突厥联盟本质上是流动、多变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首领手中,而非集中在可汗手里。因此,当突厥武力进犯中原时,各部多各行其是,缺乏步调一致的行动。虽然突厥可汗往往对中原抱有极大野心,但他无法向其他部落首领保证每次由他发起的军事行动都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行动遭遇挫折或失败,他的领导地位就会动摇。由于无法犒赏和保护其追随者,[17]他很容易受到内部摩擦或内战的影响。唐廷重视突厥各部的细微差别,避免视其为一体,并充分利用突厥联盟的弱点,瓦解其阵营。[18]唐廷曾数次离间突厥各部或是突厥与其盟友的关系,阻止其采取联合行动,从而化解了突厥的攻势。
唐代统治精英十分了解游牧民族和边疆社会。游牧民族四处迁徙,逐水草而居。他们根据自身与唐的实力对比,时而臣服唐廷,协助唐的军事行动,时而反叛唐廷或调整与其他游牧部落的关系。唐人与游牧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的人比中原百姓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相当自由地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经常对各个试图统治他们的政权都表示效忠。[19]无序流动和多重效忠因而成为边疆社会及其民众的特点。[20]唐代统治精英非常清楚,流动性是边疆游牧社会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常态,因为他们的祖先就出自那里。不过,他们常常以贬低性的言辞来表达对游牧民特有的流动性的认识。他们声称,游牧民贪婪、鲁莽,不知忠诚和友谊为何物,对礼仪更是一窍不通。
对辽阔边疆地区及其民众流动性的洞识成为唐朝防御战略的基础。唐朝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唐廷有限的资源导致唐无法永远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与其划疆定界,不如对边疆地区实行松散管理,只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墙。[21]不过,修筑防御工事不是要将敌人拒于门外,而主要是监视敌人的动向,并提醒朝廷可能的入侵。如果确实是入侵,唐军便退入城中固守,并伺机组织反击。[22]
这种防御战略预示着唐朝的对外关系会经常处于“不战不和”的不稳定状态。由于唐和它的敌人都既无力承担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无法维持永久的和平,因此即便在唐占据相对优势时,双方也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唐廷为确保更大的外围地区的安全而设置了“羁縻州”,由降附或被击败的部落首领担任都督、 刺史等。这些部落首领依然保有对本部落的统治权,但须接受唐朝官员的监督。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基于精明的计算——既然唐廷对边境部落的军事胜利和失败的部落首领的政治效忠都是暂时的,那么无论是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唐朝的区划,还是用唐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当地的统治机构,都是不明智的。唐军虽然能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未必可以永远取胜。而“羁縻”制度则可以使唐廷灵活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投降的部落再次反叛,唐廷也能从容应对。
唐朝君臣按照“知己”的原则仔细评估自身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并据此确定了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他们还得出结论,唐朝若对四邻的利益置之不理,则不可能有效促进自身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和谐”, 或称“相互的一己利益”。这一观念强调,唐朝官员必须对某个时期唐与四邻的实力对比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宜的对外政策。这样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带来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种强调“合宜”“功效”的处理外交问题的方式,看似违背了唐廷一贯用来为自己的外交动机和行为辩护的“德”“义”等普遍道德原则;但实际上,唐朝战略思维的“合宜”“功效” 和作为道德诫命的“德”“义”是并行不悖的,因为适用于某时某地某个具体情况的对外政策正是“德”“义”等抽象道德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国家行为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因为它体现了政治的最高道德——在行动之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毕竟,政治道德是以结果来评价政策的。
从上述讨论可见,唐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实用多元主义,而不是某一位皇帝对世界的宏大道德构想,这种教条式的构想显然不足以成为观察多元世界的工具。尽管唐廷惯于用一种普世性的道德目的论来包装其对外政策,但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以理想主义为表,以务实主义为里,是道德原则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逐渐改变和调整的产物。这些改变与意识形态偏好无关,其本质是演进的,目的是使唐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唐在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时,如何制定出协调、均衡的对外政策,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就必须从多极、相互的一己利益、相互依存、合宜的视角考察唐与四邻的关系。
注释
1.当代学者用“契约忠诚”来形容这种效忠关系。它的存在“取决于双方是否履行各自的义务”,而且“双方在判断对方是否信守承诺时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见Jonathan Karam Skaff,“Survival in the Frontier Zon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in China’s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Sui-Tang Dynastic Transition(617-630)”,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5,no. 2(2004),p. 134;Charles A. Peterson,“P’u-ku Huai-en and the Tang Court: The limits of loyalty”,Monumenta Serica,29(1970-1971),p. 445。
2.崔瑞德注意到“唐朝的朝贡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四邻的自愿参与,后者的目的是从一个比自身富裕得多的社会谋求经济利益”,见Denis C. Twitchett,“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in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edited by Hans van de Ven(Leiden,2000),p. 147。
3.吉娜·L.巴恩斯指出,东亚各政权是独立发展的,并不总是与外界互相关联,也不是唐高层次文化单向传播的结果,见Gina L. Barnes,China,Korea and Japa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New York,1993),p. 8。唐朝时的契丹和奚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两个游牧部落活跃在今辽宁省。在该地区发掘的墓葬显示,从初唐到704年左右,当地墓葬习俗受到当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此后,当地的汉式墓葬逐渐减少,八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更是完全消失。这些变化表明,当地游牧部落的势力及文化影响力在稳步增强,而唐朝在辽东的影响力则在逐渐减弱,见辛岩:《辽西朝阳唐墓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第2期, 385-386 页。
4.这一现象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见Nicola Di Cosmo,“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3,no. 4(1994),,1116。
5.Denis C. Twitchett,“Sui and T’ang China and the Wider World”,in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 3,pt. 1 of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Cambridge,1979),,37。还可参考他的“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
6.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9页。
7.小约瑟夫·奈将现代外交中的软实力定义为“无须借助有形的威胁和回报而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这种实力是团结他人而非胁迫……用行为学术语来说,软实力就是吸引力”,见Joseph S. Nye Jr.,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2004),pp. 5-7,44,111。但笔者认为,在前近代,软实力必须结合有形的回报和利益才能发挥作用。
8.汉斯·摩根索称这类政策的“目的是以征服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为手段,改变国家之间的实力关系”。但这一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例如,西班牙曾对拉丁美洲进行文化渗透,但这种渗透对实现其帝国主义的目标并没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西班牙缺乏必要的军事手段,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与拉丁美洲的权力关系,见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Brief edition,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Boston,1993),p.75,p.82。
9.例如,八世纪时回纥修建了一座有十二扇巨大铁门的城市作为牙帐。一份八世纪五十年代末写就的回纥文献也记载了两座回纥城市,见Denis Sinor,Geng Shimin,Y. I. Kychanov,“The Uighurs,the Kyrgyz and the Tangut(Eigh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 4,edited by M. S. Asimov and C. E. Bosworth(Paris,1998),。还可参考Minorsky,“Tamīm ibn Baḥ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p.283。汉文史料记载,回纥早在八世纪之前就开始建造城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59,1026页;《资治通鉴》,卷211,6722页,卷226,7282页。关于古代在今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修建城市的研究,见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p.251。
10.川本芳昭:《五胡における中華意識の形成と『部』の制の伝播》,《古代文化》第50卷第9号,1998年,4-7页;《五胡十六国·北朝期における胡漢融合と華夷観》,《佐賀大学教養部研究紀要》第16号,1984年,1-24页。后来回纥也出现了类似的“权力中心论”。回纥统治者认为其权力来自“上天”,来自“月神”和“太阳神”,并“声称对一切民族享有统治权”,见Colin Mackerras,“The Uighur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edited by Denis Sinor(Cambridge,1990),p.326。隋代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以“天子”自称,认为自己是上天所生,统治“世界四方”。他还用“大”“智”“贤”“圣”等字形容自己,见Mori Masao,“The T’u-chüeh Concept of Sovereign”,Acta Asiatica,41(1981),,50-58,72-73。
11.关于“权力中心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及日本兴起的综合研究,见酒寄雅志:《古代東アジア諸国の国際意識》,《歴史學研究別冊特集》,東京:青木書店,1983年,25-34页。这一观念在渤海国(勿吉)出现的时间是五到六世纪,在新罗的出现则是在新罗完成朝鲜半岛统一之后的七世纪后半期,见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東京:校倉書房,2001年,440-441页。
12.关于“日本中心论”的兴起,见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451-459页;川本芳昭:《漢唐間における「新」中華意識の形成—古代日本·朝鮮と中国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0号,2002年,1-26页;朱云影:《中国华夷观念对于日韩越的影响》,《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5年第8卷第 11期,51-52页;Wang Zhenping,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关于民族中心主义在东亚国家发展的讨论,见川本芳昭:《四―五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天下意識》,载田中良之、川本芳昭编:《東アジア古代国家論》,東京:すいれん舎,2006年,277-297页。中译见川本芳昭著、汪海译:《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2007年,179-200页。
13.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125-126页;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437-438、450页。
14.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442-446页。
15.Wang Zhenping,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
16.在军事文化领域也出现过类似的相互交流又相互竞争的过程,不过在这里唐朝是借鉴者,唐在战争中采用游牧民族的策略以对抗他们的骑兵,见Jonathan Karam Skaff,“Tang Military Culture and Its Inner Asian Influence”,in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Cambridge,2009),。另见氏著:《何得“边事报捷”?》,载柯兰、谷岚、李国强编:《边臣与疆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1-30页。
17.杰勒德·查理安德注意到:“每位新的游牧部族(联盟)首领维护自己权威的方法,是组织和发动成功的军事行动,使(自己与联盟其他部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每次这样的军事行动之后,)他就能够以较从前更有利于己的条件,(与联盟中的其他部族)订立新的契约。”见Gerard Chaliand,From Mongolia to the Danube:Nomadic Empires,Translated by A. M. Berrett(New Brunswick,2004),p.23。
18.例如,突厥部落联盟即由十部(即所谓的“十箭”)组成。这些部族成员的身份认同的基础主要是政治而不是族群,见Mackerras,The Uighurs,p.320;David Sneath,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 of Nomadic Inner Asia(New York,2007),p.108。彼得·高登为大卫·斯尼思一书撰写了书评。他在书评第295页指出:“当代有关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研究大都认为所谓‘部落’和‘氏族’是复杂现象。它们涉及多种要素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又多呈不稳定状态。”高登的书评还列举了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其他重要著作。
19.马克林以西域的北庭及其他一些城市为例说明这一问题。这些地方看似“在回纥的势力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可能近乎完全自治或是在唐的保护下”,见Mackerras,The Uighurs,p.328。
20.David Ludden,“Presidential Address: Maps in the Mind and the Mobility of Asi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2,no. 4(2003),。关于七世纪六十年代中亚地区民族迁徙的研究,见Twitchett,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p.118。
21.在中世纪,边疆指地带或地区。“边疆演变的方向并不总是从带状到线状,相反,两者常常共存,服务于不同目的”,见Nora. Berend,“Medievalists and the Notion of the Frontier”,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2,no.1(1999),。另见Daniel A. Bell,“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oundaries: A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erspective”,in States, Nations, and Borders:The Ethics of Making Boundaries,edited by Margaret Moore and Allen Buchanan(New York,2003),;Ling,l. H. M,“Borders of our Minds: Territories,Boundaries,and Power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in States, Nations, and Borders: The Ethics of Making Boundaries,edited by Margaret Moore and Allen Buchanan(New York,2003),。
22.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Boston,1962),;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1958(Oxford,1962),,113-116,257。斯加夫将这一策略称为“纵深防御”,见Skaff,“Tang Military Culture and Its Inner Asian Influence”,。另见程存洁:《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唐研究》第3卷,1997年,363-379页。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加】王贞平/著 贾永会/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后浪2020年6月版
1.《37唐朝专题之好书·书摘丨唐朝如何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37唐朝专题之好书·书摘丨唐朝如何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51855.html